日本東京都知事豬瀨直樹,因涉嫌收受醫療團體「德州會」的五千萬日圓非法政治獻金,在強大輿論壓力下,宣布辭職下台。這在日本既非空前,也非絕後!
日本是一個講究「恥感」的民族,但不具有「罪感」的文化。「罪感」是來自本我的要求,發自內心的道德信仰來約束自己的行為;而「恥感」卻是來自他人的壓力,依靠外來強制的力量來約束自己的行為。這也難怪,長久以來,許多日本政治人物因為違法收受政治獻金,在「恥感」的催迫下紛紛被迫下台。對日本人來說,在不被外人發現之前,或者外界未出現譴責的聲浪時,都不能算是一種罪過,這是日本人恥感文化的特殊性。
然而,日本人的恥感一旦被掀開,就如同打開潘朵拉的盒子,就會被社會無限膨脹與放大。這像是一種集體催眠,在聽到和鳴的聲音之後,便會轉化成為共同的信仰;更像是一種無形的教條,在潛移默化下,便會轉化成集體的社會壓力。
先前,豬瀨直樹風塵僕僕為東京申奧奔忙,其間連妻子過世時都不眠不休,不僅成為東京申奧成功的最大英雄,更成為僅次於安倍的高人氣日本政治家。然而,在收賄事件爆發後,霎時有如豬羊變色,豬瀨如同過街的老鼠,人人喊打。日本輿論要求他下台的聲浪,如排山倒海而來,彷彿只要豬瀨繼續在任一天,便會使東京奧運在國際社會蒙羞。日本人對於恥感的無限上綱,於此可見一斑;日本人的重恥感、輕人情,更是有目共睹。對豬瀨直樹來說,可謂成也申奧,敗也申奧。
日本人的重恥感,來自於社會集體的約束力;而日本人的輕人情,來自於清楚的法律分際。我們看到,日本人通常會說誰的行為是不符合哪條法律,卻甚少抱怨制度不公不義;我們也看到,日本人會說誰違反哪一項規範,卻極少譴責裁判者自私不仁。這使得日本人能夠在這種極大的心態的轉換下,不會產生任何的陰影;這也使得日本人在這種急遽的行為轉變上,而不用背負任何的人情包袱。
一旦恥感形成了特定氛圍,日本絕對不會因為事屬「微罪」而輕輕放過。例如,前日本外務大臣、也是民主黨時期的明日之星前原誠司,便曾經收受家鄉相識多年的韓裔女性區區二十萬日圓的政治獻金,被發現後,便倉促宣告辭職下台,日本輿論界對他亦不表任何惋惜。
一旦犯行超越恥感的界線,日本也絕不會因為某人職位崇高,而有所妥協。例如,民主黨執政後的首任首相鳩山由紀夫,便曾因假造政治獻金名冊,而面臨辭職壓力;最後雖未被檢察官起訴,但日本政壇亦未作任何挽留。政治獻金無疑是日本政治人物的慣常遊戲,但稍有逾越卻成為豬瀨直樹致命的悲劇。
由此可見,在日本政治的遊戲規則中,除了法律,社會約束力以及輿論壓力仍是一道重要的防線。這種輿論壓力,讓政治人物在法律之外必須要以高道德標準來檢視自我,而沒有理盲濫情的空間。同時,這道社會的約束力,也讓日本政治人物在被掀開遮羞布之後,必須負起該有的政治責任,不可能因人情世故而脫逃。
從豬瀨直樹的辭職看王金平的關說案,儼然形成強烈的對照。豬瀨在收賄事件爆發之初,曾辯稱是單純的朋友「借款」,同時也提出借據及簽名自清;但在輿論、東京都議會及特搜組的強大壓力下,豬瀨最後選擇辭職下台,以保住自己最後顏面。反觀王金平院長關說案,在國內媒體的理盲及民眾的濫情下,竟被無限上綱成馬政府的政治追殺,在野黨更搖旗吶喊助陣,嚴厲討伐偵辦關說的司法人員。由此可見,台灣的政治人物不但沒有罪感,更喪失了恥感。
簡言之,日本人雖然沒有「罪感」,但終究還保有「恥感」;日本雖然政治弊案層出不窮,但社會輿論的注視和約束卻成為最有力的一道防線。反觀台灣人的恥感,在濫情的人情世故糾纏下,扭曲不全;台灣社會的集體約束力,也在藍綠的政治對決下,蕩然無存。
有人說,十年前的日本就是現今的台灣寫照;但是,從政治人物的知所進退看,現今台灣就連這點恥感也看不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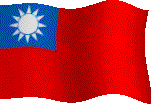

 本城市首頁
本城市首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