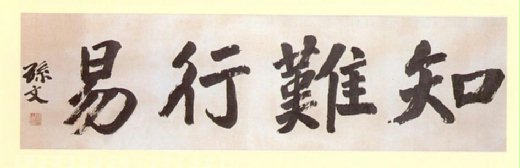辜振甫、汪道涵相繼謝世,象徵一個時代的結束。「後辜汪時代」該如何化解近十年來的兩岸僵局?
前不久,前陸委會副主委陳明通在國父紀念月會上表示,未來兩岸可參造「歐盟統合模式」解決歧見;陳水扁總統隨後指出,歐盟模式可以做為選項。北京大學國際關係學院教授牛軍在接受《中國時報》記者訪問時指出:目前民進黨的執政導向,仍然強調「台灣主體性」,也就是朝「台獨」的方向操作。從這點來看,現在提出「歐盟」模式,接下來肯定要搞修憲,因為歐盟的邏輯就是「一個國家,一個憲法」。
確實,陳水扁在闡述「歐盟統合」的意義時,便強調:「每一個會員國都是主權獨立的國家」,「所有會員國,沒有大小之分,不能說有一方是國家,另一方不是國家」;這種「一個國家,一個憲法」的主張,顯然無法解開兩岸間的僵局。其實,歐盟的發展並沒有什麼固定的「模式」。我們要借重歐盟經驗來解開兩岸僵局,必須堅持「一中兩憲」的原則,不能搞「一個國家,一個憲法」,也不能搞「一國兩制」。
「一中兩憲」不是「一國兩憲」,因為一個國家不可能有兩部憲法,「一國兩憲」根本違反了政治學原理。「一中兩憲」只是在描述當前海峽兩岸客觀的政治現實。更清楚地說,自從一九四九年中華民國政府撤退到台灣之後,海峽兩岸便分別各有一部「中華民國憲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這兩部憲法都是建立在「一個中國」的原則之上,雙方並各自據此而建立一個「中華民國政府」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兩個政府間未簽訂任何的和平協定。
從政治學的角度來看,任何政治實體都必須用憲法來加以界定。如果海峽兩岸當局都能夠接受「一中兩憲」的政治現實,彼此承認對方為政治實體,雙方便可以平等的地位展開談判,建立兩岸間和平穩定的互動架構,不必擔心誰會「吃掉」誰。
「一中兩憲」的主張,是建立在憲政自由主義的精神之上。唯有憲法可以作為檢驗兩岸關係發展最重要的指標。更清楚地說,中共一九八二年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而其「前文」又指出:「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實質上即無產階級專政」,這樣的憲法跟在台灣所施行的「中華民國憲法」,正如油水之不能相容,目前兩岸根本沒有統一的條件。
然而,憲法也是人訂的。不僅台灣的「中華民國憲法」曾經多次修改;即使是對岸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也有一九四九年的「共同綱領」,以及一九五四、七五、以及七八年等不同的版本。
「一中兩憲」的重要涵義之一,就是以憲法做為檢驗兩岸關係的標準,雙方各自堅持自身憲法中所宣示的「一個中國原則」,但也各自保持修憲的權利。目前,我們可以「一中兩憲」為基礎,來建構兩岸間和平穩定的關係;將來可以再依時局發展,依民主的程序,決定要不要再制定一部「中國憲法」,逐步達到統一目標。
「一中兩憲」的主張進可以攻,退可以守,是解開兩岸僵局的良策。現在問題癥結在於:阿扁是不是願意接受「一個中國原則」?(作者為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一中兩憲 不爭統獨 爭制度

黃光國∕台大心理系教授(台北市)

在元旦談話中,陳水扁表明將啟動第二階段憲改,期望在二○○七年舉辦新憲公投。接著又透過立法院長王金平邀請國民黨主席馬英九組閣。明眼人一看就知道:阿扁是一面用新憲公投穩住深綠的陣腳,一面向馬英九挑戰:即使把組閣權讓給你,你對兩岸關係又能提出什麼對策?
在我看來,藍軍領袖習慣性的反應:回歸「九二共識,一中各表」,無法和阿扁修憲主張對抗。陳水扁早已說過,未來的新憲公投將以「中華民國是台灣」作為主軸。相形之下,「一中各表」除了「一個中國原則」之外,對兩岸關係並未提出具體主張。目前,中共將「一中原則」表述成「一國兩制」,這種將台灣「香港化」的主張,泛綠群眾和大多數中間選民怎麼可能接受呢?
藍軍領袖對兩岸關係提出的政策,包括馬英九的「一國兩區」,宋楚瑜的「兩岸一中」,以及新黨的「一國兩治」,在綠營看來,和對岸的「一國兩制」並沒有實質上的不同,根本忽略了「台灣主體意識」,所以泛綠陣營會視之為是「賣台集團」在和中共「隔海唱和」!
我所主張的「一中兩憲」則不然。它強調:目前兩岸便分別各有一部「中華民國憲法」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兩部憲法都是建立在「一個中國」原則之上。只要在野陣營堅持「一中兩憲」原則,對內可以對抗阿扁「中華民國是台灣」的修憲主張,對外可以對等政治實體的立場和中共展開談判,建構兩岸間穩定的和平關係。
許多人反應:「中共會接受嗎?」我的回答是:這樣的主張旨在捍衛台灣的主體性,對岸當局即使心中不樂於接受,恐怕也很難說出口。為什麼呢?
「一中兩憲」的主張只是在描述當前兩岸客觀的政治現實,並沒有違反「一個中國原則」。更重要的是:在中共反國家分裂法通過之後,如果我們將中華民國憲法中的「一中原則」修掉,中共便可能「採取非和平方式及其它必要措施」,對台灣動武。更清楚地說:中共的反國家分裂法其實是「愛屋及烏」,為了反對法理台獨,為了堅持一個中國原則,而不得不保障「一中兩憲」的現況。他如何能夠反對這樣的主張?
「一中兩憲」的主張是建立在憲政自由主義的精神之上。中華民國憲法第一條:「中華民國基於三民主義,為民有民治民享之民主共和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一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是工人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的社會主義國家」,兩者正如油水之不能相容,兩岸並沒有立即統一的條件。未來兩岸關係的發展應當以憲法作為判準,雙方各自保有修憲的權利,等到兩部憲法修到彼此可以相容時,再依民主程序,決定要不要制訂一部「中國憲法」,逐步達到統一的目標。
這樣的磨合過程可能需要二、三十年,甚至更久。然而,只要台灣堅持「一中兩憲」,兩岸關係便可以由統獨之爭轉為制度之爭。將敵我矛盾化為內部矛盾,兩岸兵戎相見的危機便可能化解於無形。
馬英九當選國民黨主席時,提出「一國兩區」,泛綠陣營問他:「二○○八年是要選特區區長,還是選台灣總統?」日前他接受國際媒體訪問又表示:統一是國民黨的終極目標,卻沒有提到「一中兩憲」的限制條件,受到阿扁一陣奚落。身為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卻不懂得以憲政自由主義捍衛「台灣主體意識」,不管他敢不敢接受阿扁的「組閣」挑戰,都得當心成為綠軍的箭靶!
【2006/01/05 聯合報】
聯合筆記》國家認同有問題

羅嘉薇

陳水扁總統元旦談話楬櫫兩岸經貿政策新思維和二○○七年「新憲公投」的國家總目標,有人嘆息,有人痛罵;但也有人額手稱慶,欣見總統又回到正確的道路上。兩極反應,當在談話人意料中:早說都是國家認同的問題。
「積極開放,有效管理」政策變成「積極管理,有效開放」,有舊文字新組合的趣味;但府院隨後詮釋,三通和開放大陸觀光客來台政策未變,管理是為開放準備,聽來又像新瓶裝舊酒。其實,企業西進的經濟理性,哪裡是政府管得了的?開放暫時做不到,就說管理優先,算是自我安慰,也保留喊價籌碼。
國家認同的市場區隔,才是陳總統為重出江湖選擇的主戰場。在反省地方選舉慘敗的那些天,陳總統若以歷史為師,勢必想起二○○四年三月,他如何以認同政治當唯一選戰主軸,輔以和平公投,領導基本盤居於弱勢的民進黨贏得勝利。那場經典戰役,證明認同政治風險雖大,但獲利頗豐。
在元旦談話前八天的十二月廿三日,陳水扁早就大談國家認同的重要。他說,來自內部的國安挑戰,追根究柢只有一項,那就是「國家認同」問題。他更引述一項民調說明,到一九九八年,認為台灣前途只有台灣人民才能決定的民眾已達百分之八十一,認為大陸十三億人也有權參與的只有百分之十三,顯示僅有「百分之十三左右的民眾依舊堅持著舊有的國家認同。」
回歸國家認同問題,陳總統似乎就有居於多數的自信。這在以「新台灣人」自詡的馬英九看來,雖不清醒,卻有一定的實證基礎。馬主席說統一是國民黨的終極目標,難怪陳水扁見獵心喜,因為在二○○四的認同對決中,連宋早被迫不再提統一,甚至主張國統綱領和國統會體制的調整可以討論。
有人不能苟同,更多人不堪其擾,但認同政治在台灣就像結不了痂的傷口,變成泛藍的阿奇里斯腱,拉誰打誰的想像某種程度也附著其上。陳總統再出手,這回要細火慢燉,透過一萬場憲改座談的教育工程把熱度延續到二○○七甚或二○○八。對馬主席時代的國民黨而言,已形成全新的課題和挑戰。
【2006/01/05 聯合報】
 你那裡懂了?
你那裡懂了?
 回應給:
回應給:  Aquila(Aquila)2006/01/17 16:20 推薦1
Aquila(Aquila)2006/01/17 16:20 推薦1 |
| 看得出你是不怎麼懂 你不過是調子唱的不刺耳 想藍綠共鳴 左右逢源而已 人與人之間 可與言則與之言 還有下一句呢 網路上互動 人若主觀太重〔如台灣上面就是有個國家〕 思辨混濁〔如父親是黃埔的 自己當然是中華民國的紅五類〕 格調猥瑣〔如可以原諒支持共產黨革命的大陸人民但不原諒共產黨及肯定共產黨統治的台灣人民〕 風度不佳〔如某某某某我看不起你 你給我撤銷對我的推薦....〕.... 又愛搶佔制高點上談事論人而言不及義自以為是 譬如說 開口就是人性啊 良心啊 民主啊 和平啊..... 閉口就是真善美啊 理性啊 忍啊 孔子啊 佛說啊.......及《網路城邦發言守則與禮節》說 我是寧可站這種人的在相對面上〔無恥〕 也不願與那動輒以之恥人者打交道的 該尊敬的尊敬 不該尊敬的就不尊敬 我認真執著想殺了你 毀你的家庭 搶你老婆 你也尊敬我這愛的精神嗎 凡心存欲叛我民族分裂我中國者 任何人皆無可受中國人之尊敬 共產黨即縱禍中國殃人民 亦不成中國人可以在台灣自搞中華民國在台灣獨立於中國之外的理由 國民黨即縱五十年造福台灣 亦無與民進黨共擁台灣而思遠離中國之理 愛中華民國在台灣獨立者 是以不可變不可為之共產黨統治事實為其暗搞台灣獨立之煙霧 以漸求脫離中國而可無愧疚於自己先人與中國廣大人民也 王金平曾言獨立是選項 馬英九近日言統一是選項 但對一個真愛自己中國之中國人言 不是僅止於相信將來中國會統一 應是矢志以赴的目標....並促使全中國人民過更好的日子 |


 本城市首頁
本城市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