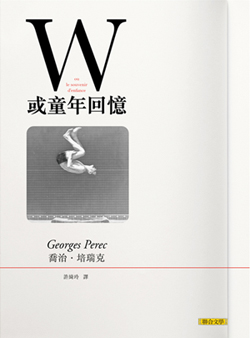
I
我遲疑了很久,終於要述說我的W島之旅。如今,我決心寫下來,是出自迫切的需要,堅信我曾親眼見到的那些事,該被揭露出來,攤在陽光下。我並非故意裝傻,佯裝不知種種似乎想反對出版的顧慮──或「藉口」才是我要說的,但也不知為什麼──。我看見了什麼,長久以來我一直想保守秘密;因為,或許由於人家交託給我的使命並沒有達成──但又有誰能做得到呢?──,何況託付我使命的人也已消失無蹤,也就不該由我來散佈那樁使命的任何內容吧。
我曾猶豫了很久。我已漸漸忘了那趟旅程中不明確的曲折遭遇。然而,我的夢中卻一直充塞著那些幽靈城市,猶在耳邊響起的是陣陣喧囂的血腥競賽,歷歷在目的是飄揚空中、被海風撕裂的小方旗。不解、恐怖、迷惑,交纏在無底的回憶中。
長久以來,我一直在為我的故事尋找蛛絲馬跡,我參閱了無數的地圖與年鑑,也查遍了零碎片段的檔案資料,但卻什麼也沒找到,有時感覺自己只是作了場夢,僅有的,就是一場難以忘卻的惡夢。
……年前,在威尼斯玖蒂卡島 上的一家小飯館,我看到有個我以為認識的人走進來,我趕忙衝向他,但即刻又三言兩語,支吾著向他道歉。不可能會有殘存者!我的雙眼看到的,曾經確確實實發生過:蔓藤穿裂了嵌板,樹林吞噬了房舍;沙塵侵入了運動場,成千上萬的鸕鶿襲捲而過,接著,四下無聲,突然一片冰冷死寂。不管發生了什麼事,不管我作了什麼,我都是唯一的承受者,唯一的倖存記憶,是那個世界獨留下來的遺跡。就因這點,遠超過任何其他的考量,讓我決定寫出來。
專心的讀者從上文推斷,一定會明白我打算見證的那件事,我只不過是個旁觀者,不是主事者。我不是我的故事的主角。我也不能算是我的故事的吟詠者。即使我見到的事顛覆了我原本微不足道的生命歷程,即使這些事仍整個兒重重地壓著我的一舉一動,左右了我看事情的方式,但為了述說它們,我打算援用種族學者冷靜平和的語調:我探訪了那已沉沒的世界,而這就是我的見聞。縈繞著我的,不是阿夏柏沸騰的怒氣,而是逸胥邁耶的白日虛夢,或是巴托比的沉著。繼許多人之後,又一次,我請求他們作為引領我的幽魂導師。
話雖如此,為了滿足一個幾乎已成通則,而我也不想再爭論的常規,現在,我盡可能以最簡略的方式,先提示我的幾項生平重點,更確切言之,是交待在什麼情況之下決定了我的那趟旅行。
我於一九……. 六月二十五日,約莫凌晨四點鐘,出生在離A.不遠,沒三戶人家的小村落R……。我父親擁有一小片農地。他因受傷引起的併發症而死去,那時我還不足六歲。除了債物,他什麼也沒留下來,我所得到的遺產就是幾張票據,少許衣物,和三、四個碗盤而已。我父親有兩個鄰居,一位主動收養了我;我就在他家長大,半像兒子,半像個農場的雇工。
我十六歲那年,離開了R.到城裡去;有段時日,工作換來換去,但始終沒有找到合意的事做,最後當兵去了。因我一向習於服從,身體又比別人耐操,本來可以當一名好軍人,可是我很快就明白,我永遠不會真正適應軍隊的生活。我在法國T.的訓練中心待了一年之後,被派往戰地;我又繼續待了十五個月多。一次在V.休假時,我開溜了。經由一個拒服兵役者組織的安排,我得以前往德國,但在那裡好長一段時日,工作一直沒著落。最後,我在非常靠近盧森堡邊界的H.安頓下來,在城裡最大的修車廠找到了一份加油工的差事。我住在一家小小的寄宿家庭,晚上下工後的時間大多耗在一家酒館看看電視,偶而也和我的這位或那位同事玩玩骰子棋戲。
II
我沒有童年回憶。大約到我十二歲為止,我的故事只要兩、三行文字就可總結:我四歲喪父,六歲喪母;我在維拉德隆 幾個不同的寄宿學校度過了戰爭時期。一九四五年,我父親的姊姊和她先生收養了我。
故事的闕如,長久以來教我安心:因故事客觀而乏味,表面上一切明瞭,一副天真無辜的樣子,再再都保護著我,但是保護我免於什麼傷害呢?莫非就是我的故事,我活過的故事,我真實的故事,屬於我的我的故事,可以想見,那故事既不乏味,也不客觀,表面上也不明瞭,顯然也並非無辜?
「我沒有童年回憶」:我這樣肯定的表示,確信如此,幾乎帶有某種挑釁的意味。別人可不准拿這個問題向我質問。這問題不在我的規劃中。我早已躲過了:因為另一個故事,大的故事,帶有巨斧的大寫歷史,已經代我回答了:那就是戰爭、集中營的歷史。
十三歲時,我編造、描述了一個故事,也畫了出來。之後,我全忘了。七年前,有一晚在威尼斯,我忽然回想起來,這個故事叫作W,而就某方面來講,它若非就是我童年的全部故事,也至少是我童年的故事之一。
除了突然想起了標題,我對W幾乎沒留下任何回憶。我全部的所知僅在於這句話:火地群島有個小島,島上的社會生活完完全全只為了運動著想。
又一次,書寫的陷阱已佈局好了。又一次,我像個孩童在玩躲迷藏,卻不知自己最害怕或最渴望的,到底是哪一樣:躲藏好,還是被人發現?
後來,我找到了幾張十三歲時畫的圖。有了這些畫,我重新編造了W的故事,寫了下來,以連載的形式,從一九六九年九月到一九七○年八月,陸續發表於《文學雙週刊》 上。
四年過去了,今天我打算對這漫長的解讀過程作個了結──我的意思是要「劃出界線」,同時加以「命名」。W和我的奧林匹克幻想並不那麼相似,同樣的,奧林匹克幻想與我的童年也不更為相似。但是在這兩者交織的網絡中,以及我為了此事讀的書當中,我知道,就在那裡刻印著、描述著我所曾行經的道路,我的故事緩緩前行,我緩緩前行的故事。
III
我待在H. 已三年了,一九xx年七月二十六日早上,房東遞給我一封信。這封信是前一晚從距離H. 約五十公里外一個略具規模的城市K.寄過來的。我打開來看,是用法文寫的。紙質極佳的信紙上印有箋頭名號:
奧圖.阿費施塔爾 MD
上方有個複雜的盾飾圖樣,刻工完美,可是我不諳紋章學,無從辨讀,連簡單的解讀也作不到;事實上,在五個象徵組合當中,我只能清楚認出其中兩個:一個有雉堞形的塔樓在中間,和整個盾紋一般高,而下方右側,一本翻開顯出空白頁的書;其他三個象徵圖形,縱使我費盡心力想要看明白,卻依然隱晦不明;但這可不是什麼抽象的象徵,比方說,不是人字形,也不呈帶狀或菱形,而有點像是具有雙重面向的圖形,是一種既精確又曖昧的圖畫,彷彿可用多種方式來相互詮釋,卻又無法決定一個令人滿意的選項。其中一個,非要講的話,可看成一條扭曲的蛇,身上的鱗片又有如桂樹;另一個可視為一隻手,同時又像是樹根;第三個,既像鳥巢又像火盆,要不就是個荊棘頭冠,要不還可能是一株火棘灌木,或者尚且也像是被刺穿的心。
信紙上面沒有地址,也沒有電話號碼。信文僅僅寫道:
先生:
若蒙首肯,接受我們拜訪,以便談論一件與您有關的情事,我們將感激不盡。
我們將於七月二十七日週五下午六時起,在位於紐姆貝格街十八號的貝格霍夫旅館酒吧間恭候您。
在此先向您致上萬分謝意,並因此刻尚無法提供您更完整的說明而深表歉意。謹向先生您獻上我們最忠誠的致意。
接著是幾乎無法辨識的簽名,只有靠信紙箋頭上印的名字,我才得以認出這簽名應該就是「O. 阿費施塔爾」。
不難想見這封信令我馬上害怕起來。我的第一個念頭就是想逃,我一定是被認出來了,很可能這是在勒索。後來,我總算控制了我的恐懼感,這封用法文寫的信並不表示一定是寫給我的,不一定是寫給以前那個成了逃兵的我;我目前的身份是羅曼裔的瑞士人,會說法語沒什麼特別奇怪的。那些幫助我的人並不知道我以前的姓名,況且只有在極不可能、又難以解釋的各種條件配合之下,才可能有我先前生活中認識我的人會找到我、並認出我來。H.不過是個小村,離主要的幹道很遠,觀光客根本不知道這個地方,而我大白天都在修車廠的汽車地溝裡度過,不然就是躺臥在引擎下方。再說,要是有人經由不可想見的偶然才找到我的蹤跡,又能向我要些什麼呢?我又沒錢,也不可能有錢。我曾參與的那場戰爭已經在五年前結束了,極可能我早已被赦免了。
我試圖以最平靜的態度來設想這封信可能暗示的種種假設。這會是一場漫長而耐心的探尋結果,逐漸縮小範圍到我身上嗎?他們以為是在寫信給借我名字的那個人嗎,或說,我與他同名的那個人?某位律師會以為我是一筆巨大財產的繼承人嗎?
我把那封信一讀再讀,想要每次發覺多一點的線索,可卻只找到令我更好奇不解的理由。這個寫信給我的「我們」是一種書信慣用語,如幾乎所有的商業書信所延用的慣例,而署名者是以其受雇的工作單位之名在發言呢?還是對應兩個、多個的通訊者?接在箋頭「奧圖.阿費施塔爾」名字後的這個「MD」又是什麼意思?我向車廠的秘書借了辭典查詢。原則上,這個詞只可能指美語中「醫學博士」的字母縮寫,但這個簡稱雖通行於美國,卻沒理由出現在一名德國人的信紙箋頭上,即便他是名醫生;不然,我得假設這位奧圖.阿費施塔爾雖是從K.寫信給我,卻不是德國人,而是美國人;這本身並不奇怪,移民到美國的德國人很多,而許多美國醫師的原籍是德國或奧地利;可是一名美國醫生要找我作什麼?他為什麼跑來K.?如何想見一名管他什麼國籍的醫生會在他的個人信紙上標示他的職業,可是一般人對一名醫學博士會想得知的相關資料,如通訊處、他的診所地址、電話、看診時間、他的醫學專業領域等等,卻被一個如此古舊而晦澀難懂的紋飾所取代?
一整天我都在自問該如何是好。我該不該去赴約?是不是要馬上逃走,到別的地方去,去澳大利亞,或是去阿根廷也好,重新開始一段非法的生活,再捏造一個新的過去,一個新的身份,作為脆弱的掩護?幾個小時下來,我的焦慮逐漸轉成了不耐與好奇;我焦躁不安,想像這次見面將會如何改變我的生活。
晚上我花了些時間待在市立圖書館翻閱辭典、百科全書、年鑑,希望能找到關於奧圖.阿費施塔爾的消息,看看「MD」有沒有其他意義,還有那個紋章的意涵何在。可是我什麼也沒找到。
第二天早上,我被一種揮之不去的預感所困,在旅行袋裡塞了些衣物,還有,說來若不是太寒酸的話,還有我自認為是最珍貴的一些財物:我的收音機、一個據說很可能是從我曾祖父傳下來給我的銀製懷錶,一個在V.買的珠貝小雕像,還有一只稀奇古怪的貝殼,是某一天我在作戰時的教母寄給我的。我要逃亡嗎?我沒這麼想:只是想準備個萬一。我告訴房東太太說我可能要離開幾天,同時付清了該付的房租。我去見了老闆;跟他說我母親過世了,我得回巴伐利亞的D.去為她辦喪事。他准予我一星期的假,又預付給我還差幾天才到的一個月月薪。
我到車站,把袋子存放在自動寄物櫃。然後在二等候車室裡,差不多是坐在一群準備前往漢堡的葡萄牙工人中間,等著晚上六點鐘到來。
──本文收錄於喬治.培瑞克《W或童年回憶》
本文於 修改第 3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