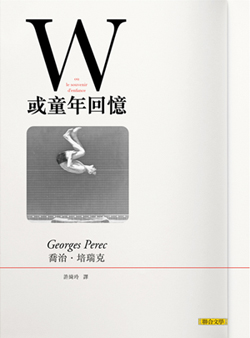
《W或童年回憶》推薦序
哀郁的文字玩家 李煒(陳青/譯)
a
就在本文開篇時,一場派對也隨即上演。看看來賓們的穿著,還有那滑稽可笑的髮型,你一眼就能判斷出這是在一九六○年代中期。
你滿耳聽到的都是法文。聯繫其中的含義,以及說話者的表達方式,就可以確定這裡的大多數人士都是知識分子,而你則位於巴黎市中心。在法語世界裡,再沒別的什麼地方能欣賞到對文化事項如此激烈而精妙的辯爭。
可還沒等你聽出爭論的主題,注意力就已轉移到其他地方。你發現自己正注視著一位身穿長袍、表情孤傲的老人。他就座於人群正中心,卻又超然游離,只揮揮手指便將所有對話的開場白拒之門外。
你正要打聽這位穿著不合時宜的老人是誰時,注意力又再次分散了,這次是轉移到那蓬鬆——應該說爆炸式的髮型上。它讓你想起了愛因斯坦的標誌性髮式:桀驁不遜、逆勢而上,只不過更加濃密,簡直像個熱帶雨林。
當你的目光轉移到狂野森林下的那張臉時,立刻會被一雙大眼睛迷住。它們炯炯有神,卻又溫柔祥和,讓自己的主人看上去異常和藹可親、平易近人。也正因為如此,在來賓如雲的派對中,你不知不覺地走向了他。
接著你做了自我介紹。可別被他謙遜卑微的態度所迷惑,那背後隱藏著無比犀利的睿智。犀利到就在他隨著你的漫談微笑點頭之際,便能道出你使用某一個詞,甚至某一個字母的頻率。
他的名字,不用說,就是:培瑞克(Georges Perec)。除了培瑞克,還有誰如此精通文字?
e
夜已深,一雙手正緩緩翻動著書頁。那不是隨便找來的什麼書,而是關於卡巴拉教的一本厚冊。
是誰在翻閱關於猶太神祕主義最隱祕的一個分支的資料?是你之前在派對上遇到的那位嗎?有可能。他無疑精通這門學問,還在自己的《漏字文歷史》中對它的寫作方法進行了精深闡述。
不錯,漏字文。這是培瑞克畢生的嗜好之一。這種文字遊戲要追溯至古希臘。基本說來,就是在寫作中刻意省略某一個,或某幾個字母。而這種寫法最大的用處可能只是為作家提供更多方式來炫耀自己的機敏。
這也解釋了為何本文也應該寫成一篇漏字文,每個章節都省略掉標題部分的元音字母。但這種寫法太費精力,在中文裡也看不出效果。但既然我們寫的是培瑞克,就讓我們假設這也是一篇漏字文吧,因為再也沒有別的方式更適合向這位酷愛文字遊戲的法國作家致敬了。
恰巧也出於這個原因,令他更像是中世紀的卡巴拉學者。卡巴拉學者沉迷於希伯來語言,試圖破解猶太教聖典的祕密含義。他們把每個詞都分解為組成它們的希伯來語字母,計算這些字母的數值(例如,把希伯來語第一個字母的值定為1,第二個的值定為2,依此類推),然後重新組合出一個新詞,或者用相同值的其他詞替換。他們希望通過這種迂迴之術,能更加貼近雅赫維的思想,並揭示他的祕密信息。
與昔日的神祕主義者一樣,培瑞克也沉迷於字詞和字母,並也對直觀含義之外的東西癡迷不已。但跟卡巴拉學者不同的是,他完全沒有宗教信仰,儘管他是波蘭猶太移民的後裔。正因如此,他才一心一意地玩起了文字遊戲。拆字遊戲、回文遊戲——只要你說得出的,培瑞克都曾玩過。他還專門幫一本雜誌創造縱橫字謎多年。
對他這樣一個癡迷於文字的人來說,加入「文學潛能工坊」(Oulipo)是再自然不過的。在走進這個「工場」之前,我們必須繞個彎子,先去一下古希臘,因為那裡不僅是歐洲文化的老生產地,也是潛在文學工場的主要供應商之一,提供了像「語言危機」這樣的話題。
對這話題最敏感的古希臘哲學家也許要算是克拉底魯(Cratylus)。他確信宇宙間所有可感知的事物都處於一種不斷變化的狀態,隨時在變動。雖然從赫拉客賴脫(Heraclitus)開始,大家都瞭解無法兩次邁進同一條河流的道理,但在克拉底魯看來,甚至連一次邁進同一條河流都是不可能的。就在你踩進去那期間,河裡已經流淌著另外的河水。
既然萬事萬物都在不斷改變,就不可能掌握任何可靠的知識,也不可能進行任何有意義的談話。所以克拉底魯才認為自覺自願的保持沉默是唯一負責任的行為,也因為如此,他簡化到把手指擺動作為唯一的交流方式。可惜的是,講述這段軼事的亞里斯多德(Aristotle)沒有說明克拉底魯用的到底是哪根手指。是大拇指嗎?用來表示「好」和「壞」。還是食指,用來指向這裡或那裡?抑或是中指,用來……唔,據說古希臘人已經在用這個手勢來表達類似當代的意思了。
不管怎樣,從古希臘的柏拉圖(Plato)到現代法國的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一連串西方哲學史上鼎鼎有名的人物,都會為這個關於語言局限性和實用性的問題——語言是否有能力指向自身以外的東西——感到不勝其煩。
i
從最基本的層面來說,語言危機無非就是:當一切事物——不論有無價值——都已經一次又一次地寫過、評過、爭論過後,該怎樣去落筆?正如培瑞克曾經問過:「在兩千名作家用盡各種方法向你描繪了『夜晚的美妙』之後,你要怎樣再說一遍?」
但這顯而易見的事實並沒得到多少知識分子的認可。他們大多懼怕被冠以「頭腦簡單」之名,堅決不願說些平實而基本的東西。波蘭哲學家柯拉柯夫斯基 (Leszek Kolakowski)在做出下列這番俏皮的評論時,無疑有所指:
那些不喜歡園藝的人需要理論支撐。缺乏理論、單純的不喜歡園藝是一種空洞、毫無價值的生活方式……相對於沒有理論基礎的不喜歡園藝,另一個選擇就是種植園藝。但掌握一種理論,比真的去種植園藝要容易得多。
這些反覆引用的有關理論的說法又把我們帶回了二十世紀的法國。畢竟,法國人是出了名的善於理論化和過於理性化。正是一位法國人為了自己的存在與否而焦慮得緊握雙手,然後以典型的法式伎倆,通過思考自己存在而「證明」了自己的存在。
也許就因為這樣,在過去一百五十年裡,許多法國著名的知識分子都曾與這種假定的語言危機較過勁。但到了二十世紀中期,這個陳陳相因的主題卻又呈現出新的緊迫性,因為當時法國的尊嚴正岌岌可危。
二戰之後的法國,仍傾覆在戰敗德國的餘震之中顛蕩。糟糕的是,法國本土文化也同時處於戰勝國美國的包圍之中,英語外來詞彙四處充斥,吞噬著法國社會的各個層面。僅從一個簡單的事實就能看出法國人對這一轉變的厭惡:早在十七世紀時,法國人就已經設立了法蘭西學院這樣的機構,它那時唯一的宗旨就是保持法語的「純度」。顯然,二戰後法國人最迫切關注的事態之一就是打造一個能再次令他們引以為榮的「園林」。為此,必須有人來種植園藝。
既然是在法國,一個滿是知識分子的國度,他們立刻爭辯的問題並不是「哪些人」有資格擔任園丁,而是這些園丁應該「怎樣」著手開展自己的工作。換句話說,要仰仗於哪一套園藝理論?
o
培瑞克在一九六○年代開始發表作品時,受到的正是這種局勢的影響。當時有三大理論可供在法文這片土壤上耕耘。
首先是薩特(Jean-Paul Sartre)學派。在二戰結束後不久出版的《什麼是文學》中,這位知名哲學家提出,所有文字作品都必須包含某種觀點,因此作者不可能避開自己作品中暗含的政治和倫理看法,即便他想要這樣。既然不能推脫,就應該「負起責任」,為正義事業而戰,為人性昇華而努力。
而另一邊,則組成了所謂的「輕騎兵」(les Hussards),一群如今已遭遺忘的作家。他們都是根深蒂固的右翼分子,存在的唯一理由就是對左翼分子薩特的一切表述深惡而痛絕。既然勁敵呼籲「承擔責任」,輕騎兵就別無選擇,只能倡導一種「毫不承擔責任」的文學。換句話說,一種「為了藝術而藝術」的文學。
第三方是格裡耶(Alain Robbe-Grillet)和那些「新小說」(le nouveau roman)的追隨者。這些作家在一九五○年代中期聲名雀起,幾乎顛覆了有關小說定義和小說功能的一切傳統理念。他們尋求一種新的文學,可以通過貶低——甚至統統破除——故事裡的人為因素來更加忠實地反映現實,從而去關注以前遭到忽略的事物,例如那些構成傳統小說背景的靜物。
對生於一九三六年的培瑞克來說,上述三個選擇似乎都不理想。他不可能拜薩特為師,因為他對政治的興趣轉瞬即逝。他也不能忍受輕騎兵,因為一直以來他都偏向左翼。他對新小說作家的體驗派作品也沒什麼好感。像他這樣的年輕作家該走向何方?幸運的是,在培瑞克面前已經鋪好了一條小路。鋪路的是一個當時仍寂寂無名的團體,成員主要是法國作家,他們稱自己為Oulipo。
這個聽起來奇怪的名字是幾個法語單詞的首字母縮寫:「Ouvroir de littérature potentielle」,直譯為「文學潛能工坊」。這個走在前沿的團體成立於一九六○年,成員的目標是通過借鑒數學方法並向正在撰寫的作品強加限制來擴大書面表達的可能性。
從表面上看,第二個說法尤其違背常理。按照嚴苛、怪異的新準則寫出來的書怎麼可能「解放」作家的想像力,並促進文學的創造性?但進一步細看,這個想法無疑令人震撼。其實,所有的文學作品都遵循這樣或那樣的寫作慣例,而這些慣例面世之初,想必都讓人覺得莫名其妙。就說詩歌吧。如果不是嚴格按照繁瑣而貌似無理的規則寫作散文,如今會有那麼多家喻戶曉的詩人嗎?
誠然,潛在文學工場所提供的這種解決語言危機的方法,仍不能讓克拉底魯這樣對語言已經絕望的人再次開口。但對於那些立志寫作的人來說,它卻能輕易幫他們解決「夜晚的美妙」這個問題。作為潛在文學工場的創始人之一,奎諾(Raymond Queneau)不就做了最好的榜樣?在他那本無比巧妙的《文體練習》(Exercises de style)一書中,就向世人展示了如何以九十九種不同的方式講述同一件事。
對培瑞克而言,潛在文學工場對文字遊戲的熱情以及對形式創新的重視尤其令他心動。這很容易理解——由於沒有相應的學術資格獲得晉陞,在他短暫的成年生涯中,大多時候都只能在一間實驗室擔任圖書管理員。因此,如果文學潛能工坊派真的是「一群喜歡與自己修建的迷宮挑戰的老鼠」(他們的早期自我表徵),那成了這個工場派的培瑞克本人,最終也能逃離那夢魘般的工作,在閒暇之時走進自己精心打造的文字曲徑。
u
培瑞克四十五歲時接受了一次英語採訪,他在採訪中宣稱自己「想要以任何可能的方式講述任何事物」並「進入所有文學領域」,甚至包括連環漫畫和兒童書籍。這樣,當他走完一生時,就能「用盡字典裡的所有詞彙」。
在接受採了訪半年後,培瑞克就死於癌症,再也無法實現自己的夢想。然而,他還是留下了大量的文字。
他最知名的作品仍是玄學偵探小說《消失》(La Disparition),在這本書裡他沒用到一個最常見的法語字母——e。儘管這一重大障礙導致他僅能選用不到20%的法語詞彙,培瑞克仍寫出了一本琅琅上口的小說。在該書首次出版時,唯一費時審閱它的批評家都沒有發現自己讀的居然是一本漏字文小說。(後來培瑞克為這部小說寫了一個簡短的姊妹篇,除了e,其他所有元音字母都沒用。雖然寫作難度更大,但由於句法複雜、對話做作,還有對慣用拼寫法的不時嘲弄,這部作品並不如前一篇成功。)
在培瑞克的作品中,野心最大的一部就是巨幅小說《生活使用說明》(La Vie mode d'emploi)。故事在巴黎的一座公寓內展開,一間間、一層層地講述住客的經歷。小說遵循一種複雜的敘事體系,映射出國際象棋中「馬」的棋路。這本書真正的成就在於,儘管繁雜異常,充滿各種各樣的想法和遊戲、瑣事和題外話,卻極易閱讀。
而自我流露最多的要屬培瑞克的《W或童年的記憶》(W ou le souvenir d'enfance)。這部非典型自傳體小說有部分寫於作者接受精神治療期間,其中兩則看似無關的故事,最終匯集到一個納粹毒氣室上。(培瑞克在二戰期間失去雙親:他的父親為保衛法國戰死沙場,母親則死於集中營。)
但他也寫了不少百無聊賴的作品,其中包括充滿了自製詞的廣播劇;記錄他在一年時間裡吃喝過的所有東西;81種「簡易菜譜」的排列遊戲;還有480個句子全都以「我記得」開始的回憶之書。他自誇從不在自己的作品中兩次使用相同的「公式」或「體系」,而事實上與此相反,培瑞克喜歡編目錄和列舉。這也許和他擔任全職圖書管理員有關。可以確定的是,每當他沉浸於此的時候,他的作品就遭殃了。他想做到詳盡無遺,卻只落得精疲力竭。
面對如此不平穩的表現,培瑞克在文學史上究竟該如何定位?
也許他沒有格諾那樣的幽默感令作品生輝,沒有馬修斯(Harry Mathews)的抒情天賦,沒有魯博(Jacques Roubaud)的文思敏捷,也沒有卡爾維諾(Italo Calvino)的哲學深度。他可能也不如胡塞爾(Raymond Roussel)或雅里(Alfred Jarry)——他的個人偶像,也是文學潛能工坊的前人:既沒有前者獨特的創造性,也沒有後者奔放的想像力。但他的確同時具備上述六位的基本特質。事實上,他是連接這六顆耀眼群星的唯一線條。光憑這一點就能讓培瑞克躋身文學巨匠。可時至今日,他仍遭到某些文學派別的冷遇、輕視、忽略。原因何在?
y
嚴格說來,y不是元音字母,儘管必要時也可以充當。這樣的靈活性對熱愛文字遊戲的人來說,無疑是個天賜之物。這篇假裝是漏字文的小品文也剛好缺少一個「尾聲」,而且在引出本文的那場虛構的派對上,還有另一位嘉賓在場。他遠離人群,像個人類學家一樣,全神貫注地在一旁觀察。
他就是凱洛依斯(Roger Caillois),曾寫過一本名為《遊戲與人》(Les Jeux et les hommes)的書。凱洛依斯以荷蘭歷史學家赫伊津哈(Johan Huizinga)的早期成果為基礎,在這本書中提出了六個所有遊戲的共同特徵。首先,遊戲絕不能是強制性的。其次,遊戲必須與其他活動區分開來,例如工作。第三,遊戲的結果不能確定,要留待遊戲者即興發揮。第四,遊戲必須受自身規則控制。第五,遊戲必須在某個層面上涉及一個與現實不同的虛假世界。
到這裡一切都好,但還有第六個特徵,難免會引發培瑞克這類作家的疑問。據凱洛依斯所說,遊戲還必須沒有產出,「既不製成貨物,也不創造財富,或者任何類型的新要素……結束時要回到遊戲開始之初的情形。」
如果是這樣,那培瑞克創作的那些文學潛能工坊派作品——也就是說,他大部分的作品——又被置於何地?僅僅是微不足道的瑣事嗎?而培瑞克的心血也毫無價值?
就在培瑞克去世前不久接受的那次採訪中,他將文學潛能工坊派定義為把文學「當作玩樂、當作遊戲」的人。當然他緊接著補充到,對於文學潛能工坊派來說,玩樂和遊戲本身就是「正事」。
無論這種說法多麼實在,核心問題依然突出。就算培瑞克對自己的遊戲很認真,那些遊戲除了自身的規則以外,是否又認真地看待其他事物呢?而文學——最起碼名副其實的文學——又該以什麼方式,從哪裡切入「遊戲與人」之間的這種二元關係呢?
這並非老生常談,強調文學必須包含一些道德教義、真知灼見和事實真相。只是要指出,沒有語言以外的維度——沒有超越字面的潛力——任何作品無非就是一個展示創作者獨創性的櫥窗。對那些次要的潛在文學工場派作品而言,也許連這種獨創性都值得懷疑。因為作者在創作過程中艱難克服的障礙——強加的限制——都由作者自己所創建。這就像自己回答自己的問題,還沒提問就已經知道答案。
再說,卡巴拉學者之所以沉迷於文字遊戲,是為了尋找雅赫維。而對薩特、新小說派,甚至輕騎兵而言,當一天結束時,甚至在他們所寫的一切都消失之後,他們仍有可仰仗的理想和信念。
相比之下,培瑞克對這些完全不感興趣。吸引他的是謎題、文字把戲、詞彙和結構創新。他只為遊戲癡狂。儘管如此,在他最好的作品中,仍然成功插入了文字以外的維度,讓這些作品不僅只是機敏的文字發明,不僅「只是寫作,在白紙上書寫字母」——借用他在一部非小說作品中的說法。
若非如此,這一切又有何意義?除了它的漏字文花招,如果《消失》不具備一個更深的層面:寓指二戰期間數百萬猶太人寂寂無聲的「消失」,與那些普通的驚險讀物相比,這本小說究竟又有何差別?
也許正因為這樣,培瑞克常常看起來並不怎麼快活,即便他總是深陷於這樣那樣的遊戲。原因可能不僅在於他把玩法看得太過認真,還在於在他心中,總是懷疑玩樂和遊戲並沒有真的為語言危機提供一條出路。
難怪照片裡的他看起來總是那麼憂鬱,即使是在微笑的時候。因為他那雙充滿感情的眼睛,雖然看似柔和,卻也充滿了哀傷。而這種哀傷一再顯現,甚至在他最為逗樂的作品之中。讀完他的文字之後,你難免會感到遺憾。遊戲結束了,面對的又是生活,而在這生活裡,誰又能給你一本真正的《使用說明》,協助你走出自己的迷宮呢?
──本文收錄於喬治.培瑞克《W或童年回憶》
本文於 修改第 3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