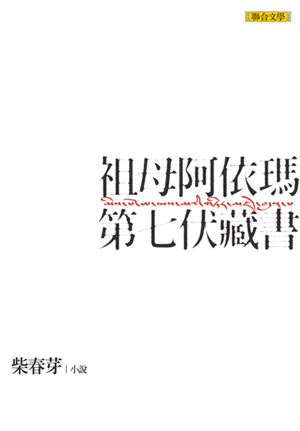
九月的一天晚上,一陣歌聲將她從夢中驚醒。她躺在睡袋裡靜靜地聆聽著。窗外有雨。一個夜行人在雨中的水泥路面上踟躕。風,搖響了布達拉宮寂寞的風鈴。她的聽覺如此敏銳,可以捕捉宇宙的節律。歌聲在房子裡如絲如縷地飄蕩著。一個男人用那種能讓冰雪融化的好嗓音唱著一首古老的西藏情歌。這首歌的旋律是如此熟悉,但她卻又一時想不起來她第一次是在哪裡聽到的。她想:也許是在某張音樂CD上聽到的吧。她聽過許多歌。少女時代,她在美國紐約,跟離異後的母親住在一起。她聽搖滾樂,偶爾吸食大麻。他的初戀情人——一個來自英國有著貴族血統的少年——提出分手的那天,她把自己關在房子裡不顧母親的勸解反復播放一首西藏民歌。那是個傷心欲絕的夜晚。聽歌之前,她跟自己打賭說,如果在隨便聽了某一首歌之後,還是無法平息內心的創傷,她就割腕自殺。水果刀就擱在枕頭上。結果,那首西藏民歌挽救了她的生命。無意中購買的一張CD,那首西藏民歌夾雜在葡萄牙民歌Fado和吉普賽民歌Flamenco當中。自那以後,她就瘋狂地迷戀上了西藏民歌。她聽了許許多多的西藏民歌,但她卻不懂每一首歌的意思,因為她不懂藏語。如今,在拉薩,在九月的拉薩之夜,在這間被她經營了半個世紀的酒吧房間裡,到處都是西藏民歌的CD。她聽得懂CD中的每一首民歌。許多年前,她孤身一人來到拉薩,為的是學會藏語。可是,此刻正縈繞在房間裡的這首古老的西藏情歌,她聽了很久,只聽出零星的幾個詞語,卻沒有聽出什麼意思。這首歌並非來自某張被她收藏的CD。到底是誰在她獨自一人居住的房子裡唱歌?她回想十二點以前發生的事情。她不記得有誰留在房子裡。十二點以前,她送走最後一位因為愛情受挫而借酒澆愁的漢族旅行者,然後關上酒吧的店門,打開睡袋,在木頭地板上睡著了。她忙碌了一天,又陪那位口口聲聲要以自殺祭奠愛情的漢族旅行者喝了幾瓶啤酒,還唱了很久的歌,所以睡得很香。她忘了自己在十二點以前唱了一首什麼歌。近來,她總是如此健忘。很多次,她手指縫裡夾著香菸還到處找菸盒。剛剛擦過的地板她會再擦一次。這是衰老的象徵。很久以來,她總是失眠,偶而睡著,又被蝙蝠的尖叫或者地球運轉的噪音吵醒。這都是衰老的象徵。她難得像今天晚上睡得這麼香甜。可是,一個男人唱著一首古老的西藏情歌,將她吵醒了。她有些懊惱地起身,赤裸著身子,用右腿撐著地面,一跳一跳的,在房子裡走來走去。她伸出雙手,觸摸著空氣,企圖摸著歌手的脈搏或者呼吸。她在這間房子裡自由行動,避開桌椅和柱子。她熟悉這個房子,就像熟悉自己的身體。許多年前,她買下這個二樓的木頭房子,將其改造成了一個酒吧。她之所以要買這個房子,是因為有個朋友給她複印了一份噶廈政府的檔。檔中說,這個房子原本屬於達賴喇嘛的一個侍者,解放軍進入拉薩的那一天,他在這個房子的房頂上豎起了一面五星紅旗。達賴喇嘛率領十萬藏人逃亡印度以後,這座房子落進了一名漢族官員的手中。但在民間,有一種傳說,認為這間房子曾是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經常光顧並偶爾夜宿的地方,因為他最鍾愛的情人瑪姬阿米就住在這裡。他為情人瑪姬阿米寫下過動人的詩歌:在那東山頂上,升起皎潔的月亮,瑪姬阿米的臉龐,浮現在我的心上……那時候,她癡迷西藏的一切。她覺得,這樣的老房子肯定裝滿了沉甸甸的歷史。酒吧裝修好了之後,她就把自己的家搬了進去。這個家滿是書籍、電影DVD和音樂CD。為了解決睡覺的難題,她準備了地毯和一套被褥。如果天氣變冷,她就鑽進睡袋。在拉薩漫長的歲月裡,她一直過著這樣簡樸的生活。在她還是貌美如花的年紀,如果不是經常有情人在這裡過夜,她幾乎算得上是個苦修的僧尼。那時候,她把掙來的錢全都花在了登山運動上。那是一項屬於富人的運動,但是,對一個天性孤獨的人來說,花錢在登山運動上,有利於治療她那可怕的厭世症和自殺癖。很多次,她獨自一人帶著登山用具去攀登大大小小的雪峰。曾經一度,她覺得自己不再孤獨。這種感覺持續了半個世紀之久。可是,在九月一個有雨的夜晚,聆聽著突然響起的歌聲,她感到從未有過的孤獨撞擊著自己脆弱的心肺。她倒沒有害怕,在被時間的小白蟻快要侵蝕殆盡的記憶裡,她模模糊糊地想起,曾有一位跟她銷魂一夜但在黎明的曙光裡消失不見的喇嘛告訴她,說拉薩的每一間老房子裡都有鬼魂出沒。那都是些善良的鬼魂。她總是這樣想。那些鬼魂的心裡埋著佛的種子,因為在鬼魂們還是人的年代,佛教在拉薩相當興盛。時遷事移,鬼魂已經沒有什麼可怕的,可怕的是那些用暴力追求西藏獨立的年輕人。這些年輕人當中,有失業者,有大學生,也有四處流浪的僧人。她好幾次遇到過他們的威脅。她也親眼目睹了他們毆打手無寸鐵的漢人。雖然達賴喇嘛尊者一再反對暴力,但是,將近一個世紀過去了,這種狀況絲毫沒有改變。也許明早醒來,她會發現那個借酒消愁的漢族旅行者就躺在街角,被人割斷了喉嚨。時至今日,這樣的凶殺案在拉薩仍然時有所聞。毫無疑問,兇手是那些追求西藏獨立的青年。他們認為所有的漢人都是侵略者。他們認為所有的漢人都應該為歷史上被解放軍殺害的八萬藏人付出血的代價。總有一天,西藏會血流成河。歷史總是給活著的人們賜予仇恨而不是智慧。她想到這裡,憂心忡忡地從枕頭邊摸出香菸和打火機。她一邊抽菸一邊聆聽那首古老的西藏情歌。唱歌的人彷彿一縷空氣。他比自己的歌聲還要輕盈。聽著聽著,她覺得這首歌的旋律變得越來越熟悉。她好像曾在哪兒聽過這首歌。她甚至覺得自己曾在某個夜晚唱過這首歌。或許,很久以來,這首歌就一直盤踞在她的腦海裡,像一粒幻聽的種子,扎根在大腦深處。如果說這首歌是一種幻聽的話,她就有理由懷想一個人,一個幻想甚於現實的人。嚴格地說,那是她年輕時代遇見的第一具屍體。一具美麗的屍體。她記得,那年在雅拉雪山,她攀上巨大的冰川,看見了一個罹難的登山者。罹難者是個藏人。巨大的冰川成了他的棺材,成了他鏡子一樣透明的家。他是那樣年輕,高大,俊美,彷彿只需一聲溫柔的召喚,他就會從酣睡中醒來。她不知道這西藏美男子緣何葬身冰川。或許,他是某支國際登山隊的嚮導;或許,他是個神山聖湖的朝拜者;或許,他是當年保護過達賴喇嘛出亡印度的遊擊隊員;或許,他是三百年前神祕失蹤的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可是,誰知道呢,弄不好他只是個為情殉命的癡心少年。他的死亡凝固了時間。像是對待一個相愛已久的戀人,她俯身在冰川上,親吻著埋住了他面孔的那塊冰面。她想擁抱他。一種強烈的情欲小獸一般舔舐著她的子宮。她想和他在星空下做愛。她想和他生下一個藏漢混血兒。她自作主張,為他取名叫俄日朵。那天晚上,她在冰川上紮下帳篷。流星雨劃過月亮的陰暗面,降落在雪山上的俄日朵峰。冰川上流淌著星星的眼淚。大約在子夜,有人唱起了一首古老的西藏情歌。歌聲時遠時近。疲憊不堪的她似睡似醒。她一直以為自己在做夢。她一直以為,那個葬身在冰川下的美男子復活以後,正在冰涼的世界裡為她唱著火焰般的歌。她在冰川上住了三天,每天晚上都在似睡似醒的狀態下聆聽那首古老的西藏情歌。她迷戀這個魔幻的夢。最後,在暴風雪的逼迫下,她才依依不捨地離開。回到拉薩,跟往常一樣,她在自己的酒吧屋裡迎來一個又一個火一樣的情人。在七八月的旅遊旺季,總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旅行者。她把自己獻給他們,讓他們喘息著顫抖著在她女性的胴體上開拓可能而私密的疆界。來自歐美的白人和來自漢地的文藝青年以及拉薩城裡土生土長有權有勢的藏族男子,全都成了她夜間的獵物。在那些由於騷亂頻仍而遊客絕跡的日子裡,她就把乞丐、流浪藝人、朝聖者、苦行僧和來自草原的牧人請進這間無人光顧的酒吧和他們整夜做愛。拉薩的喧囂之夜分泌出濃郁多汁的情欲。她是聞名拉薩的一頭花豹。一頭淫蕩的花豹蹀躞街頭。自從鐵路開通以後,隨著遊客如潮水般湧入拉薩,與她共度一夜之歡的男人越來越多。在此之前,她半是認真半是戲謔地對那些和她一樣來自現代化的大都市而自命為藏漂一族的人說,等到鐵路修通以後,她就離開拉薩,永遠不再回來,因為鐵路破壞了這個世界唯一具有原始之美的高原之城。呼嘯而來的火車用它的第一聲汽笛震碎了拉薩純淨如冰一樣的空氣,與此同時,也震碎了她的豪言壯語。在潮湧而至的旅遊者當中,她變得比誰都要俗氣。像水一樣在她的裸體上漂流過的男人都說她性欲旺盛得如同一頭花豹。她只是笑笑。花豹的身周,砌築於時間之上的聖城一再陷落。她的情人如此之多,但卻沒有一個情人能夠知道,她在男人的肉體上飲鴆止渴,為的是止息對俄日朵的思念。俄日朵是嵌入她身體裡的鴉片。痛苦啊,我的俄日朵!你讓這個來自異國他鄉的漢人女子所能擁有的每一個與異性交歡的夜晚都變得既蒼白又黯淡。孤獨啊,我的俄日朵!她在情人滾燙的懷抱裡隨著重疊而起的陣陣高潮尖叫著。為了俄日朵,神祕誘人的俄日朵,她再次出發,去尋找那個保存在冰川下的藏人。從看到他的第一眼起,她就不曾覺得他是個業已死去的人。那不是一具屍體。她一再安慰自己。他安安靜靜地躺在冰川裡,為的是與一個期許了愛情的人共赴生命的約會。她一遍遍地告訴自己,那是個在酣睡中做夢的情人。他那冰涼的微笑仿如一截遺留在她夢裡的刺狀物,經常讓她在一種尖銳的疼痛中悚然驚覺。可是,雅拉雪山上最高最神聖的俄日朵,不再願意接納她了。它甚至不讓她攀上冰川。每天都有暴風雪。她住在雅拉雪山下的小學校園一間木制的閣樓裡,透過窗戶日日眺望著俄日朵。樓下的教室裡傳來志願者洪亮的領讀聲和孩子們清脆的朗讀聲。志願者是個詩人。他畢業於一所名牌大學,當過報社記者,編輯過民間詩刊,主辦過詩歌網路論壇,突然有一天,他告別都市的好友,隻身一人來到雅拉雪山腳下這所偏僻的鄉村小學,成了一名義務的小學老師。那時候,藏人與漢人之間的種族仇殺愈演愈烈。誰也想不通這個年輕的詩人為什麼要在如此危險的情況下來到藏人居住的小村莊當一名義務的小學老師,而且在這裡一住就是好多年。好多年以後,她才逐漸明白,那年輕的詩人其實跟她一樣,堅持用愛的方式消弭藏人與漢人之間的仇恨,唯一的區別在於,她用的是肉體,而他用的則是靈魂。她應該愛上他才對。在那錯裂的時代裡,她應該愛上他才對。可是,那個適宜談情說愛的美好季節,杜鵑花才開,她卻在日日迷茫的眺望中虛度光陰。在那個季節,暴風雪時時來襲,她沒有愛上年輕的詩人,因為她的心中只裝著俄日朵。來年這個季節,她又一次離開拉薩,去尋找魂牽夢縈的俄日朵。那是她心中的戀人。她跟隨一支專業登山隊,來到雅拉雪山腳下。年輕的詩人不在校園裡。宿舍牆壁上掛著蒙塵已久的吉他。一首寫了一半的詩歌等著他來結尾。孩子們說,兩個月前,他去攀登俄日朵,從此就再也沒有回來。她的心中,一觸即發的,是尖銳的隱疼。第二天風和日麗,她隨登山隊攀上冰川。她告訴登山隊員,說她來到雅拉雪山不是為了看望那位詩人,而是來尋找一具埋在冰川下的屍體。那是個年輕的藏人,如果你睡在他的身邊,你就會在夢裡聽見一首古老的西藏情歌。登山隊員找了整整一天,那具被她一再提及的藏人屍體卻無人找見。也許是因為全球氣溫變暖的緣故,冰川以驚人的速度在消退。前年她來登山的時候,冰川的冰舌一直延伸到山下的森林邊緣,可是今年,冰舌縮回到了雅拉雪山狹長的山谷。她的俄日朵哪裡去了?雪崩的那天上午,在巨雷般的響聲中,天空崩塌了。她望著海浪般凌空而來的狂雪,一心想念的,還是她的俄日朵。後來,她頭腦昏沉,眼前呈現一片白色的暗夜。在漫長如一個世紀般的睡眠中,她隱約聽見那首古老的西藏情歌。她願意就此長眠不醒,直到把時間耗盡。當那首古老的西藏情歌消逝在宇宙盡頭的時候,她醒了。她躺在病床上。有人告訴她,與她同行的那十一名登山隊員全部失蹤了。從那以後,她不再登山了。不是她不能,而是她不想。如果願意,她會不顧一切,固執地走向雪山。她恨俄日朵。她恨所有的雪山。她恨愛情。她恨男人的肉體。只有這間小小的酒吧屋,她廝守著。有一段枯寂的歲月,讓她感覺自己突然變得非常蒼老。她曾試著凝神靜氣,希望聽到那首古老的西藏情歌。她相信,那首古老的西藏情歌會讓她重新變得年輕貌美,會讓她對男人堅硬的肉體和粗重的喘息以及刺鼻的汗腥重新煥發波濤滾滾的情欲。一切都在萎縮,花朵,時間,夢,包括可恥的愛情。對於幻聽之類的事情,她就像個聾子,因為她的聽覺也在萎縮。她的耳朵和她的子宮一樣,已經無法孕育奇妙的生命。唯有女人的第六感還保存著。在這粗糙的時代,唯有女人的第六感還保存著。知道這一點是因為她總覺得有個人在她身邊飛來飛去。一個無形無相的人。這麼多年來,她越來越覺得這間白天當作酒吧晚上當作臥室的房子有些異樣。她越來越覺得有雙眼睛在盯著她。這讓她渾身不自在。她懷疑,當她不在房子裡的時候,肯定有人來過。有幾次,她出門幾天,回來時發現家裡的東西有被挪動過的痕跡。她撫摸房子裡的一切。那株蒙上灰塵的玫瑰被擦得乾乾淨淨,連灰塵的氣味都不存留。她明明記得自己出門前忘了倒垃圾,可她回來時卻發現垃圾桶裡連個紙屑都沒有。還有一次,她坐在開往北京的火車上,突然想起煤氣灶還燒著一壺水。她連忙給一個朋友打電話,讓他破門而入,關掉煤氣。半小時後,朋友打來了電話,告訴她說煤氣是關著的,煤氣灶上放著的水壺裡,開水冒著蒸汽。好多次,她會停下手中的活,悵然若失地站在房間地板上久久久久地聆聽。她能聽見那個人在空氣中滑翔的聲音。那是一種極其細微的聲音,像粉塵墜落,又像陽光搖曳。最初的日子,她以為早年流產的孩子那未及投胎轉世的靈魂回到了這間房子。那孩子是她和一個有過一夜之歡的喇嘛悲傷絕望的果實。在她覺出自己已經懷孕的那個星期,總有一種沉重的罪惡感壓迫著她的子宮。曾有一度,她擔心腹中的嬰兒是魔鬼的種子。懷胎第七月,她流產了。她以為那孩子已經長全了五官,具備了人形,頭上還長著一對犄角。其實,那孩子在幾個月前就停止了發育。從那以後,她就斷絕了想要孩子的渴望。只是有一次,唯一的一次,在雅拉雪山,她第一眼看到那個躺在冰川裡的藏人,突然有了想生孩子的願望。那個願望像一道閃電劃過心間,很快便沉沒於她那孤獨的深淵。她的一生,註定要與孤獨為伴。如果不是屋子裡出現了一個若有若無的人,她可能再也不願回憶,不願想起逝去的年華和一張張情人的面孔,她甚至不願想起那個流產的嬰兒。她竭力聆聽。她感覺。她伸出雙手,觸摸房子裡的每一寸空氣。最後,她斷定,幾乎在每一個夜晚像一縷歌聲一樣縈繞不絕的那個人並不是她死去孩子的靈魂。那是個成年的男人。他的無形無相掩蓋不了他身上的氣息。那是一股種馬的氣息。在一個由於實施宵禁而無比寧靜的夜晚,她躺在地板上,閉著眼睛,聆聽著星星在宇宙中振動的噪音,聆聽著神靈與鬼怪在另一個空間裡連綿不絕的竊竊私語。她感覺有個人從房子的某個縫隙裡像風一樣進來。那人小心翼翼,害怕將她驚醒。他飄在空中,長久地凝視她的臉。她能感覺出他的凝視有一種灼人的溫度。她假裝睡眠,發出輕微的鼾聲。他從空中飄下來,跪在她身邊,用手輕撫她的臉。她故意翻身,讓被子輕輕滑落,露出她曾經曲線起伏而今瘦骨嶙峋的胴體。她撫摸著自己如羊的胃囊一般皺縮粗糙的皮膚,想像著它曾有過的綢緞般的質地和米一樣的潔白。許多曾和她同床共枕的男人都說,她身上有種玫瑰的香味。那玫瑰的香味總是令人陶醉。她尋覓自己身上玫瑰的香味。那香味歷經這麼多年歲月的磨礪,竟還一如當初。恍惚之間,她覺得自己身如蓓蕾。有一種甜絲絲的呼吸像蝴蝶一樣悄然臨近。她能感覺出那個人竭力壓抑的呼吸。她甚至能感覺出那人激烈的心跳。有好幾次,她猛然睜開空洞的眼睛,想要看清楚那個人到底是誰。可是,他受到了驚嚇,慌忙起身,跌跌撞撞地在木頭地板上助跑,然後搖搖晃晃地飛起來,像隻祕途的蜜蜂,在屋子裡一圈圈盤旋。你是誰?她問道。你到底是誰?沒有回答。似乎有一聲輕輕的嘆息在靜止的空氣裡濺出層層漣漪。她裸著身子一蹦一跳地在屋子裡尋找他。好幾次,她摔倒在地,可她繼續爬起來,觸摸著無處不在的空氣。他擔心被她發現。他屏住呼吸,躲在天花板上,躲在玫瑰上,躲在用玻璃球和塑膠珠串成的門簾上。他是那樣驚慌失措。這一點她能感覺出來。為了緩解他那緊張的情緒,她裝出一無所知的樣子重新躺下,蓋上被子。很快,她就睡著了。天亮醒來時,她知道那個人已經安然離開。桌上的玫瑰花被一種近似絲絨的東西擦得纖塵不染。她倚著窗戶,張開空洞的眼睛習慣性地望著樓下八廓街上稀稀落落的遊客、商人、乞丐、僧侶、朝聖者和便衣員警。她猜想那個看不見的人此刻正在遊客、商人、乞丐、僧侶、朝聖者和便衣員警中間穿過,或者不,他正貼著那些人的頭頂,搖搖晃晃地,向著某條狹長而曲折的巷子緩緩飛行。也許,他的家就在八廓街正東拐角的地方。那裡有一間三百年前修建的黃色小樓。如今,那黃色小樓變成了一個時髦的酒吧。酒吧老闆是個魁偉俊美的藏人。她與他曾經有過一段激情洋溢夜夜做愛但又為期不過一周的愛情。他與她分手時,他說她是他愛過的女人當中相處時間最長的一位,而她抹了一把他那漂亮的絡腮鬍子,平靜地說:你也是我愛過的男人當中相處時間最長的一位,因為相處時間最長,所以我最恨你。在互不來往的半個世紀之後,有一天晚上,距離達賴喇嘛逃亡印度的紀念日還差一個星期,她在自己的酒吧小屋裡接待了這位尚在人世的老情人。他在電話裡一再申明自己是個行將就木的老人。如果你的心還活著,那就請你憐憫憐憫這個準備自殺的男人。他說。其實,在死之前,我唯一渴望的,就是和你做愛,而這件艱難的事情,只有你才能幫我。於是,他們試圖做愛。用那些荒廢多年的撫愛技巧,他們迫切地需要重溫一次年輕時代的驕傲。借助於酒和春藥以及凡士林,最終,他們成功了。他們經由許久不曾有過的肉體的顫慄感覺出死亡的罌粟正在他們衰朽的大腦裡蓓蕾初綻。在一陣讓人絕望的頹喪中,她對這個疾病纏身的老情人講述了那個人。我想知道他是誰。她摟抱著老情人枯槁的身體,在他的耳邊悄聲低語。我想知道他是否愛我。過了幾天,老情人從哲蚌寺請來了一位喇嘛。透過火,他能看見神靈和鬼魂的世界。老情人對她說。他還能透過一碗水看到你的前生後世。整整一個星期,喇嘛躲在衣櫃裡。她懷著一種喜悅和激動的心情等待那個人到來。一個星期過去了,喇嘛走出衣櫃,搖搖頭,只說他看到了一個世紀前發生在這間房子裡的一樁謀殺案,至於她提到的那個人——他身上有一股種馬的氣息——他並沒有看見。她心裡明白,那個人真的沒有來,雖然她一再期望喇嘛透過衣櫃的門縫看見一個和她想像中一模一樣的人手持玫瑰向她頻頻示愛。那個人像是受到驚嚇似的,整整一年,都沒有再來。她是那麼思念他,像一個初戀的少女,以至於衰老的身體再也承受不了愛情的悲劇。她終於病了。在她的最後一位老情人——也就是那個魁偉英俊的酒吧老闆——死去後不久,她拄著拐杖由一個素不相識的人攙扶著冒雨參見完他的葬禮,她就病了。沒有人看出她的表情或者身體有什麼異樣,也沒有人察覺她的氣色有什麼不對,但她自己心知肚明。參加完葬禮,她沒有打傘,也拒絕了別人的攙扶相送。她拄著拐杖敲擊著路面顫顫巍巍走在回家的路上。人類的喧囂潮汐般在她的耳朵裡起伏。她突然聽見體內保存多年的一座建築正在迅速坍塌。這是一場致命的疾病。她嘟嘟囔囔地說。這場疾病能讓時間窒息。九月的一天晚上,客人們來酒吧時,她給每個客人送了一件禮物。那都是她保存多年的書籍、電影DVD和音樂CD。有一些來自漢地的女孩,她送她們的是她年輕時為了讓自己的漂亮獲得超現實的美學效果而用過的戒指和手鐲。她慷慨地施予,弄得這個九月的夜晚有些非現實的況味。這是最後一個夜晚。她對客人說。最後一個夜晚,我想為你們唱一首古老的西藏情歌。自然而然的,她就唱了起來。她甚至不知道她所唱出的每一句歌詞是什麼意思。大家靜靜地聽著,有人流下了傷心的眼淚。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這首歌如此憂傷。大家要求她再唱一遍。沒有人知道為什麼這首歌如此動聽。於是,她又唱一遍。哭泣聲像窗外的雨點一樣落進虛無的夜色。接著,她又唱一遍。所有人都哭了,只有她沒哭。她在那最後一夜到底唱了多久,連她都不記得了。也許是受到這首歌的感染,那位自稱是因為愛情失敗才來西藏旅行的漢族男子當眾吻了她的嘴唇。他說他愛她,如果她允許的話。她搖搖頭,微微一笑。不。她說。今天晚上,我要等一個真正愛我的人。漢族旅行者臉色蒼白。十二點快到的時候,她送走最後一位客人,也就是那位為了愛情聲言自殺的漢族旅行者,然後反鎖房門,鑽進睡袋,躺在地板上等死。過了一會兒,一陣倦意襲來,她沉沉入睡。臨睡之前,她就知道,這一次不是睡眠,而是死亡。當一個男人用那種能讓冰雪融化的好嗓音唱著一首古老的西藏情歌,將她從夢中驚醒的時候,她的意識陷入混沌。她不能確定自己是一如既往地活著,還是如她所願的那樣已經死了。她不知道誰在為她唱一首古老的西藏情歌。那歌聲讓她久已乾涸的眼睛重又濕潤起來。許久以來,她又一次品嘗到了淚水中的鹽和鹽中的西藏往事。窗外有雨。一個酒醉的夜行人在雨中的水泥路面上踟躕。風鈴,搖響了布達拉宮孤獨的神靈。她第一次驚奇地發現,自己的聽覺竟然如此敏銳,可以捕捉宇宙的節律。至於是誰在為她唱那首古老的西藏情歌,她知道,但她卻不願說出,或者,即使她說出那歌手是誰,又有什麼意義呢?在她臨終的時候,我們誰也不在。在末世的黑夜裡,我們不曾目擊,不曾見證。我們每個人都是那悲慘世界的缺席者。
──本篇小說收錄於柴春芽最新小說《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
本文於 修改第 1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