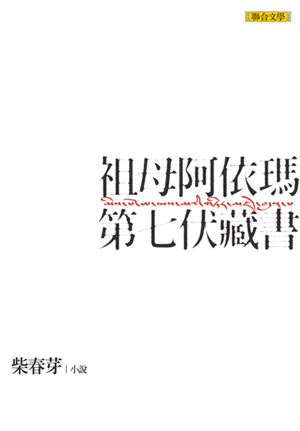
我受邀而來。卓瑪忙碌的身影偶然會在牆壁上那眾多的窗子中某一扇敞開的窗戶裏一閃即逝。沒有她的招呼,我不便擅自闖入她的家裏,何況,那只黑豹一樣的藏獒正用它陰沈的眼睛虎視眈眈地盯著我。沉重的鐵鏈在它的脖子底下嘩嘩作響。它那涎水漣漣的大口隨著一陣又一陣慵懶的哈欠而不時張開,露出鋒利如匕首一樣的牙齒。那牙齒能輕易斬斷狼的脖子。因此,我一動都不敢動,只好定定地站在塵土飛揚的路上,欣賞那極具裝飾性的碉房。從我身邊不時經過的馬隊在午後迷離的陽光裏虛幻如夢中的異獸。
由於青藏高原那獨特的、從高海拔向低海拔急遽傾斜的地形,穿城而過的河流便顯得非常急促,加之水流流量較大(夏天的雪山融水使其速度加快),兩岸又比較狹窄,河流拍擊堤岸的聲音也就非常洪亮。如果靠近河岸,人與人面對面交談,彼此之間很難聽清,除非雙方加大嗓音的分貝。在河流兩岸,木石結構的碉房鱗次櫛比。碉房那石砌的牆體(也有板築的土牆,但並不多見)外形方正,顯得古樸粗曠,與藏族男人的外表極為相像。由於碉房的牆體向上微微收縮,因而整個建築給人一種不可動搖的感覺。碉房一般分為兩層,底層為畜圈和儲藏間,上層為起居場所,包括堂屋、臥室、經堂、廚房和樓梯間。
我那迷人的卓瑪姑娘在房間裏忙碌……
碉房寬敞平坦的房頂,用來晾曬東西。一種叫「塔覺」的裝飾——纏著藍白紅黃綠五種顏色布條的樹枝——插在房頂的四角,迎風獵獵。「塔覺」的五種顏色分別代表天雲火土水(組成藏人原始樸素的唯物主義世界的五大元素)。
我站在塵土飛揚的路上,期待著卓瑪在她家二樓擺滿了花盆的陽臺上招呼我進去。杜鵑、牡丹和一些從草原上移植來的野生花卉在陽臺上開得非常鮮豔。其實,我之所以如此急切地要到卓瑪家去,是因為有個叫陳渠珍的騎士作為一名來自遠方漢地的貴客居住在這裏。他帶著他的藏族妻子西原。爆發自拉薩接著便蔓延全西藏旨在驅逐漢人的一場騷亂,一度使他們的生命危在旦夕。這是西藏歷史上的第一場騷亂。一位占卜師曾經預言,在接下來的一個世紀中,這樣的騷亂將不斷發生,直到鐵馬走路鐵鳥升空而西藏人的佛法傳遍世界的時候,這樣的騷亂才會終止。
我要見到陳渠珍騎士。這麼多年來,他是第二個出現在這個西藏小鎮上的漢人。
如果不是為了寫作這篇虛實參半、既具小說性質又有理論探索的文章,上面這幾段法國新小說派式的文字或許將永遠廢棄在某個Word文檔裏,與其一同廢棄的,或許還有我在戈麥高地上寫了一年的日記。借助那些日記,我完成了自己的處女作《西藏流浪記》。
我用法國新小說派的筆法寫過一部城市題材的小說《我們都是水的女兒》。當我試著用法國新小說派的筆法來虛構西藏故事的時候,一種錯裂的感覺,刺中了我敏感的心,使我覺得這樣的文字形同垃圾。對於魔幻的西藏,新小說派的寫作方式是一種失效的寫作方式,因為新小說派執著以求的,是用客觀的、唯物至極的筆法構築而成的文本世界,即使這個文本世界的一半或絕大部分由經驗世界的情感、理智和想像以及超驗世界的神靈、天堂與地獄組成。沒關係,新小說派會像描寫窗簾的褶皺(往往花費好幾個頁碼的筆墨)來描寫經驗世界的情感、理智和想像以及超驗世界的神靈、天堂與地獄。這難不倒他們。
可是,對我來講,用新小說派的技藝來描寫西藏,卻是一個難題,因為西藏是魔幻的。喇嘛轉世制度。女神魂湖的幻境。用整整一生在荒山野嶺苦修的瑜珈師。借屍還魂術。數不勝數的神靈與鬼怪。1883年,大持明者班瑪登德證得成就虹光身,後來,他的弟子,伏藏大師讓如圓寂時,其光蘊身縮小為六英寸許。一九五二年,德格玉隴人索郎南傑成就虹光身。其實,在西藏,像這樣證得虹光身的大成就者多得不勝枚舉。這些佛教大師圓寂時,均會出現大地振動、天布妙音、彩虹橫空等種種瑞相,而其身體大部分都化為光蘊而逝,或只留下毛髮和指甲。這是智慧的證明。自古以來,佛學智慧——人類最古老的智慧之一——養育並恩澤了青藏高原。但是,今天的漢人並沒有認識到這一點。事實上,西藏在人們的心目中從來沒有明確的概念,也就是說,西藏成了一個虛構的辭彙。這個虛構的辭彙排斥客觀的描述和理性的探究,而是容納了人們過度臃腫的關於高原風景、異域生活和神祕思想的浪漫想像。這種浪漫想像超越了事物的本質,因而具有一種魔幻的氣質。與其說西藏是一塊魔幻的土地,不如說從西藏之外來看待西藏的人是一群魔幻的人,因為這些人在唯物主義的都市生活中太過平庸,太過世俗,所以就需要西藏這個高而遙遠不可輕易企及的地域來寄託自己對於精神性生活的嚮往。正是這一點,才讓我相信,不管人墮落到何種地步,但人性中對於神性的渴望總會像深埋在地下的泉水一樣。
西藏的魔幻是一種現實。正視這個現實,對於漢人來說需要的僅僅是坦誠、謙虛和勇氣。從哲學的層面上來考察,西藏的魔幻是一種以形而上的與理想化的方式體現出的古老智慧,是一種超越了世俗性而抵達神性的生活準則。就此意義而言,西藏的魔幻使人擺脫了獸性。
西藏自十五世紀以來從未發生過大規模的人道災難。而在西藏之外,自十六世紀以降,西方開始了野蠻的殖民征服,美洲大陸上的印第安人幾乎滅絕;殆至現代,兩次世界大戰又都爆發在以文明(一種在東方人面前表現出的傲慢的文明)著稱的歐洲;在中國,幾次王朝更迭,而最大規模的戰爭——國民黨與共產黨的內戰——死傷無算;還有,納粹的屠猶事件,共產主義國家如蘇聯、中國和紅色高棉的內部清洗……西藏沒有這些人道災難,相反,十三世紀當蒙古人征服了整個亞洲的時候,西藏人用自己的智慧,不但保證了西藏不被侵略,而且還為蒙古人輸出了強大的精神資源。這種狀況在中國延續了元、明、清三個王朝。
最近半個世紀以來,西藏遭到了種種污蔑。人們不顧一個強大到連以美國為首的聯合國軍都要吃敗仗的共產帝國的侵略,而是指責喇嘛王國的覆滅是由於自身的腐朽;人們不顧西藏人被外族奴役的悲劇,而是指責西藏人不思進取;人們不顧第十四世達賴喇嘛在其自傳中對漢族兄弟姐妹的祝福與祈禱,而是指責他為分裂祖國的政治和尚。
世界上沒有任何一位政治領袖像達賴喇嘛那樣著作等身,但是,在中國,修飾他的不是哲人王的稱號,而是「披著袈裟的狼」。
我不是在為西藏辯護。
我是以一個漢族作家的良知在贖罪。
我不是在維護西藏的利益。
我是在維護人類的正義。
我不是在鼓吹西藏文明。
我是在捍衛人類最古老的智慧。
是的,人類,這個寬泛的概念在中國人的思維中一直處於缺位元狀態。我們中國人處處顧及的是,個人,家族,民族,和國家,於是,便滋生了自我中心主義、族長制、民族主義和國家沙文主義,但是,我們從來不去關心人類,我們從來不去思考在同處於地球村的時代,普世價值觀的意義究竟何在。和平與正義,僅僅停留在官方外交人員的口頭上,而不是付諸實施。因此,我謳歌達賴喇嘛不斷提倡的、由聖雄甘地的精神資源所啟發的非暴力思想。
在我寫作有關西藏題材的一系列小說時,新小說派的傑出人物——阿蘭•羅伯•格裏耶(Alain Robbe-Grilet)和克勞德•西蒙(Claude Simon)——惠澤於我的,並非他們那套怪異的寫作理論,而是他們倫理道德的純潔以及面對非正義(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殖民)而敢於批判的勇氣。中國作家欠缺的,首先是面對非正義所要付出的批判的勇氣,其次才是寫作的理論和技巧。
陳渠珍騎士率領眾人從鎮子出發時,我站在路口悵望良久。
我想回到魂牽夢縈的故鄉。
美麗姑娘卓瑪還在忙碌。她那窈窕的身影不時在窗戶裏閃現。
在陳渠珍他們走後,騷亂將在鎮子裏爆發,雖然這個鎮子上只有我一個漢人。對於這一點,我是早有預見的。也許,藏人會將我綁在木架上,用一堆篝火把我烤成油。但是,對我這樣一個上了年紀的人,跟隨陳渠珍騎士遠涉羌塘荒漠,卻是力有不逮。
這是一個藉口。
我知道,這是一個藉口。
我之所以守著這個古老的鎮子,完全是因為卓瑪。這麼多年來,我一直都在等待她長大成人。每每憶及我初次見她時的情景(從那時起,她就習慣了在牆壁上那眾多的窗子中某一扇敞開的窗戶裏一閃即逝),我的胸腔裏就會傳來一陣空蕩蕩的隱痛。這是時間之箭射穿了我的心臟所致。
我所屬意的,卻是時間之輪,因為我已接受了藏人生死輪回的觀念。如果人真像唯物主義者(他們否認靈魂,否認靈魂的再生能力與不滅的本性)所說的那樣,死後一堆灰,那我覺得生而為人當是一種最絕望、最悲慘的事情。我覺得投胎轉世是一劑治療絕望的良藥。由於時間之箭(在這個意義上,時間是線性的)的傷害,作為人,沒有理由不絕望,也沒有理由不悲傷。但就時間的相對論(在這個意義上,時間是非線性的)來說,人的存在即具有暫態性,又具有永恆性。所以,當我假設自己在一個世紀之後轉世為一個藏族修行者然後再轉世為一個名叫柴春芽的漢人時,我對此充滿了信心。
毋庸諱言,最初,也就是我開始正式的寫作之前,關於西藏的浪漫性想像壓倒了理智。或許是受到了某種過激情緒的影響,我想當然地認為西藏是一塊人間聖土,而西藏人是淳樸的、善良的、慷慨的。藏人作為漢人的對立面呈現于我的倫理觀念中,因為漢人的狡詐、偽善和自私使我覺得這是一群腐蝕人類機體的病菌。至少在三百年來,漢人對人類的精神文明毫無貢獻。我們只會貢獻暴君和騙子。而遍佈於西方世界的大小各種藏傳佛教的禪修中心,則說明西藏人對人類精神的影響力越來越顯著。
對於漢民族集體的道德淪喪,我深惡痛絕。我甚至寄希望於西藏人,希望西藏人中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或者噶瑪巴——以他們純潔的信仰來拯救漢民族,就像元朝時代西藏薩迦派精神領袖八思巴拯救野蠻的蒙古人一樣。別忘了,忽必烈曾經習慣於用漢族活人填充河渠,在薩迦班智達八思巴的建議下,這項野蠻的政策最後被廢止。自元代到清代,西藏人一直在向中國人輸出思想。西藏的精神領袖同時也是中國人的精神領袖。王力雄先生也有這種想法。與達賴喇嘛會晤時,他當面告訴達賴喇嘛,希望他不但要做西藏人的領袖,而且應該做中國人的領袖。毫無疑問,達賴喇嘛和他的列位前世一樣,是個哲人王。
達賴喇嘛是個哲人王。
這種提法是危險的,因為它必然會激起中國民族主義者們的憤怒。在此之前,不管是西藏人還是西藏以外的人,都已習慣於接受這樣一個概念,即,達賴喇嘛是政教合一的領袖,而這個政教合一的西藏社會是個神權社會,更進一步的概念是,這個神權社會高高建築在農奴制的基礎上,因此,它必然是惡的。這些概念忽略了西藏社會獨特的政治經濟模式:半農半牧以及全民信仰佛教。由於西藏乃至整個亞洲沒有發展出自己的政治思想理論,所以,一種強迫式的、自外而內的、曲解了西方原意的、後殖民主義的對於西藏政治經濟模式的界定,便理所當然地遮蔽了西藏的現實。這種遮蔽,很大程度上,是一種政治策略(殖民主義的),而不是一種文化心態。如果稍加留意,人們應當注意到達賴喇嘛治下的西藏有著極為崇高的人道風景。
印度人薩拉特•錢德拉•達斯在其著作《拉薩及西藏中部旅行記》中有過這樣一個細節:在從仲孜到拉薩的路上,在和貴族夫人拉羌談話時,「我提到驕子比鞍馬方便得多,特別是當婦女外出旅行時。但她認為把人當畜牲來使用是可恥的,並說在西藏,老百姓肯定會討厭這種做法,因為那有傷人的尊嚴。她又說,只有兩位大喇嘛(達賴和班禪)、駐藏大臣和攝政可以坐轎子,其他任何人,不論其地位有多高,都不可坐轎子。」
三年前,當我以學徒式的謙卑和獨立作家的嚴肅,開始小說創作時,我曾夜以繼日地鑽研西方文學史上的各種流派,試圖為自己混亂而薄弱的文學觀念尋找導師式的教誨。
最先,影響我寫作的,是美國一九七○年代的「BEAT一代」(中國學者將其譯為「垮掉的一代」)而不是法國新小說派。更細緻地說,是美國小說家傑克•凱魯亞克(Jack Kerouac, 1922—1969)影響了我的寫作,甚至影響了我的生活。在中國,他被尊崇為黑暗的破壞神和自由的黑天使。他影響了像我這樣生於一九七○年代的整整一代文學青年。結合中國一黨獨裁的政治環境,在缺乏新聞自由與出版自由,在做人的基本權利常被剝奪,在人的尊嚴頻遭淩辱但又無從反抗(毋寧說是無力反抗或者說是無勇氣反抗,因為一九八九年「六•四」天安門事件以血染的警鐘在每一個中國人的靈魂深處永不停歇地鳴響著)的情況下,許多人回應傑克•凱魯亞克《在路上》一書的感召,開始背包上路,開始以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反叛社會。這其中的典型,便是二○○五年七月墜落瀾滄江失蹤的詩人馬驊。他在梅裏雪山腳下一個藏族村莊的小學校義務執教一年。在他失蹤以後,新聞媒體將他渲染成一個主旋律式的、符合政府當局宣傳口徑的英雄人物。這種輕率的、蠻橫的、自以為是的報導惹怒了馬驊的諸多朋友。為了還原馬驊被扭曲的形象,許多馬驊的生前好友在網路上寫文章捍衛他反叛者和自由人的形象。這是一種與極權思維和庸俗勢力的鬥爭。而這場鬥爭一直在持續,因為極權思維和庸俗勢力對反叛者和自由人的扭曲從未停止。
今年七月,在馬驊三周年祭日,由詩人高曉濤倡導並組織了一場紀念馬驊的、主題為「最好的懷念是持續不斷地創作」的詩歌朗誦會,其意圖除了懷念一個最好的朋友之外,還有還原這位朋友真實思想與其象徵意義的舉動。我有幸參加了這次朗誦會。朗誦會在我們的蒙古族朋友阿魯斯的咖啡吧裏舉行。
在朗誦會開始之前,高曉濤播放了一部關於馬驊在梅裏雪山下的紀錄片。我看著他日常的生活情景如往日舊夢一般浮現於漸積漸厚的時光的塵埃。用三角形木架支撐的黑板上,寫著他漂亮的字跡;在課間休息時,男生在他臉上惡作劇似的塗上果汁,而女生則用她的袖角輕輕擦去他臉上的果汁;在黃昏的細雨中,他那消瘦的背影被小路盡頭的樹林逐漸吞沒……
我強忍著,沒讓自己的眼淚落下來。與在場的別人不同,我不是馬驊的朋友,在他生前,我也不曾和他謀面。當我聽著別人朗誦著一首首懷念馬驊的詩歌時,我的悲傷與別人的悲傷不同。我的悲傷來自於我和他幾乎相同的一段經歷。我在紀錄片裏看到的,是我在二○○五年八月到二○○六年八月這整整一年當中所曾經歷的生活。我理解馬驊。我理解一個人在遠離都市、親人與朋友的偏僻之地所遭受的孤獨。我理解一個人斷然割裂一貫運行的平庸生活所付出的勇氣。我最理解。我理解一個人一經作出義務執教一年的決定便要排除怠惰、退縮、失望等等情緒而堅守自己最初的承諾所需要的頑強的意志力。真的,只有我最理解。如果不曾經歷那樣的生活,誰也沒有權利說,他如何如何,他怎樣怎樣。對於西藏,人們熱衷於走馬觀花,熱衷於浮光掠影,熱衷於獵奇並在獵奇的同時向那些貧窮的藏人炫耀自己的富有和都市人的身份。
懷著敬意,我在小說《西藏流浪記》中竭力謳歌像馬驊這樣的漢人。
藏人與漢人必須有這樣一種共識,即,二者之間並不存在仇恨,藏人與漢人必須共同面對一個強大的敵人——中共官僚集團。如果沒有這種共識,藏漢兩族人民彼此都會陷入虛無的民族主義。這是有害的。民族主義乃仇恨之源,也是暴力之源。
但是,藏人與漢人一樣,在極權政治下,呈現出一種奇特的疲軟狀態。這種疲軟狀態是文學最值得探究的主題,但可惜的是,截至目前,文學出乎意料(又是理所當然的)地滯後於這種狀態。作家們(用漢語寫作的藏族作家和以西藏為題材的漢語作家)只在現象的皮膚上搔癢。
一九八○年代,曾有一批文藝青年被分配到拉薩工作。他們在拉薩形成了一個封閉的小圈子。這個小圈子基本上是把北京、上海的文藝沙龍移植到了拉薩。而有關西藏的符號成了這個文藝沙龍的裝飾物。但是,西藏人的苦難,西藏人被殖民的屈辱,西藏農牧民貧窮困苦的生活,以及西藏人反抗殖民的鬥爭(一九五八年和一九六九年的大反叛以及此後大小不等的一百四十多起騷亂事件),永遠進入不到這個文藝沙龍的議題。中國作家這種與暴政同流自甘成為御用文人的品行註定了他們不可能進入世界文學的行列。甚至,他們非但沒有在各自的作品裏(小說、詩歌、散文和繪畫等)反映西藏人的苦難、西藏人被殖民的屈辱,西藏農牧民貧窮困苦的生活,以及西藏人反抗殖民的鬥爭,反而用一種偽浪漫主義的手法「虛構」了一個被重重謊言二度虛構的由雪山、草原、寺院、喇嘛、美女、駿馬、牛羊等組裝而成的田園牧歌式的西藏。正是這個被重重謊言再度虛構的西藏在其製造者們全都撤離西藏回到內地城市過上中產階級的生活以後,吸引著一批又一批內地的文藝青年前赴後繼地進入拉薩。當他們發現西藏的真相(這個真相與醜陋、黑暗、愚昧、缺乏信任且又道德淪喪一如漢地的城市一樣)之後,一個個顯得非常失落。於是,青春的理想變為一種市儈式的投機。於是,一個個酒吧、客棧和首飾店在他們的運作下出現於拉薩街頭。這些酒吧、客棧和首飾店與西藏人無關,使它們門庭若市的,是一年多比一年的內地遊客。而藏人,連在這些酒吧、客棧和首飾店的門前歇腳都會遭到店主的訓斥。這是我親眼所見。於是,合乎邏輯的結果是,在二○○八年三月十四日的騷亂中,這些酒吧、客棧和首飾店受到了藏人的攻擊。
愛德華•W.薩義德(Edward W.Said)在闡釋文化與帝國主義的邪惡本質時,曾說「十九世紀末的歐洲人面臨著一系列有趣的選擇」。如果將「十九世紀」和「歐洲人」置換為「二十一世紀」和「漢人」,那麼,他在《文化與帝國主義》(Culture and Imperialism)一書中接下來的段落就完全可以照搬過來用以指涉如今的共產帝國的子民——漢人——與西藏的關係。薩義德說:「這些選擇都是以征服和損害土著人為前提的。一個是因為使用權利而產生的忘我愉悅——這是對遙遠的領地及人民進行觀察、統治、佔有和獲利的權利。由此又產生了冒險的遠征、牟取暴利的貿易、管理、吞併、學術研究和展覽、地方的盛會、一個殖民地統治者和專家的新興階級。另一個選擇是,貶低然後重新構造土著使之成為受統治與被管理的人。」
西藏,只是漢族文藝青年青春期一次夢遺的幻景。
西藏,是如此慷慨,成就了一批又一批來自內地的文藝青年。但是,試問:我們給了西藏什麼?
或者說,文學面對西藏,該當如何表述?
王力雄先生在其西藏問題研究專著《天葬——西藏的命運》一書中說「實際上﹐西藏問題是當今人類社會共同面臨的問題的集中反映﹐是一個合併了各種矛盾的典型病灶。」由此可見,西藏有著無限廣闊的複雜性,小說就是要探索這種複雜性,進而至於探索人是否存在著界限,因為小說力圖抵達的,就是人的界限。在小說中,我正在努力去做的,就是讓具體的國家和民族消失,因為我只想道出人類。
出於這樣的思考,我終於可以理直氣壯地回答兩位藏族朋友對我的質疑了。
一位藏族朋友對我說:你的寫作(關於西藏),是一種他者的視覺。
我從這位朋友的語氣裏嗅到了排斥的火藥味,仿佛西藏成了藏族人的一份私產,而我一再強調西藏的人類學意義。何謂他者?難道一個用漢語寫作且又隸屬于官僚體制的藏人在面對西藏真實的歷史(而非官方篡改的歷史)和藏人的苦難而保持緘默時,他(她)不是一個他者?
另一位藏族朋友在粗略地閱讀了我的小說《西藏紅羊皮書》後說:「我從頭至尾有一種奇怪的感覺,這種感覺無法跟我生活中的西藏聯繫得上,雖然人名、地名、過去、現實……似乎都很西藏,但說實話,跟我的『西藏』是隔著一層的,或者說,我的『西藏』和你的『西藏』對不上。」
作為個體的人,誰能說自己擁有整個西藏呢?
我的這位朋友出生在軍人幹部家庭,接受了全部漢語教育。她的生活從來與農業和牧業隔絕。雖說她也去過農區和牧區,但那和一個漢人浮光掠影式的西藏旅行有什麼區別。她怎能懂得收割與播種的艱辛,她怎能理解窮人(農民與牧民)的內心世界。即使排除了小說探索存在之謎與人的界限的功能,僅從我個人生長於農村並在三十歲時與戈麥高地上的牧民一同放牧的經歷與體驗來看,與那些從生到死都離不開城市的人相比,我更有資格書寫農牧社會,我更有天賦深入到農民和牧民的內心世界。我甚至可以毫不慚愧地說,我對農牧技術的熟悉和我對小說技藝的熟悉是一樣的。如果我不是因為考上了大學,從而走上另外一種人生道路的話,我會是一個侍弄莊稼的好手,也會是一個善養牲口的好牧人。我從懂事起,就開始學習農牧技術。而西藏,百分之九十的土地屬於農區和牧區。
也許,庫切(John Maxwell Coetzee)和桃莉絲•萊辛(Doris Lessing)在書寫南非故事時,也曾遭遇過非洲某些知識份子的非議,畢竟,這兩位作家是白人。但事實上,這兩位白人作家更為深沉地揭示了黑非洲被殖民的苦難,更為嚴厲地批判了白人的殖民統治,也更為豐沛地寫出了黑皮膚下的尊嚴之美與人性光輝。
我要做的是,必須積蓄力量突破某些藏族知識份子設置的這種壁壘,來繼續書寫我的西藏系列小說。
說實在的,在我進入那個名叫戈麥(官方地名是「各麥村」,隸屬於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德格縣汪布頂鄉)的高山牧場之前,我對草原生活的浪漫想像壓倒了實際的境況。那是一種艱難的生活。那種艱難不僅僅來自於物質的匱乏(沒有電,沒有通訊),也不僅僅來自於交通不便(沒有公路,出門只能徒步或者騎馬),而是來自於一種孤獨。
陳渠珍騎士是否曾像我一樣孤獨?
在我閱讀陳渠珍的傳記《艽野塵夢》時,我一再想到這個問題。
一九○九年,湖南人陳渠珍作為清王朝的一名末代騎士,隨川軍入藏,駐防工布,進攻波密,屢建奇功。那是一個動盪的時代,英軍入侵,沙俄覬覦,清王朝派兵入藏。十三世達賴喇嘛土登嘉措面對如此複雜的政治局勢,竟然保證了西藏領土的完整,不能不說是一個奇跡。隨著一九一一年武昌起義的爆發,清王朝覆滅了。藏人借助這一歷史契機,發動了第一次驅漢事件。騷亂從拉薩爆發,最後遍及西藏。陳渠珍所屬川軍自行解散。於是,逃亡開始了。陳渠珍騎士攜帶妻子西原並湘中子弟一百一十五人東歸。這一隊人馬在冬天進入羌塘荒漠,途中絕食七月,只能茹毛飲血,最後,及至到達青海西寧,生還者僅有七人。藏族女子西原像個守護女神,數次拯救陳渠珍騎士的生命。
現實往往超出了文學想像的殘酷邏輯。在陳渠珍騎士的愛情故事中,女主角的死,幾乎像是一篇拙劣小說的結尾。
關於陳渠珍和西原的愛情傳奇,並不需要我傾注過多的筆墨。我所關注的,是人與人之間在摒除了民族、文化與信仰的差異之後,純粹出於愛與慈悲的人之本性而生髮的理解與互助。
我準備就此議題寫作一篇文章,名為《一個漢族男人的生與一個藏族女人的死》。可是,這篇文章最終沒有完成。很長一段時間以來,我忙於寫作自己構思已久的幾部有關西藏的長篇小說,無暇寫作理論性的文章。為此,我覺得自己愧對了一個朋友。在二○○八年三月拉薩爆發了大規模騷亂事件之後,我的朋友才旺瑙乳希望我寫作一篇關於藏漢兩個民族和解的文章,以消除中共官方傳媒製造的民族乃至種族仇恨。事實上,在西藏底層社會,漢人與藏人一直和諧相處。漢人與藏人同是中共極權體制的受害者。那時候,在王力雄先生的倡議下,一批公共知識份子簽名抵制當局渲染種族仇恨的新聞宣傳。才旺瑙乳答應,我的這篇文章將率先在他主辦的藏人文化網刊發。那時候,藏人在漢地旅行受到了普遍歧視。
如今,當我以另一個題目,談論西藏人的智慧,捍衛西藏人淳樸善良的性格,並且鼓吹民族和解時,我覺得自己正在實現一個一年前向才旺瑙乳許下的承諾。
另外,同樣是在一年前,李敖(一個從未到過西藏的人)在鳳凰衛視大肆批評西藏的黑暗與西藏人的愚昧。才旺瑙乳就此寫作了一篇反駁文章。那時候,我應該加入戰陣,為才旺瑙乳呐喊助威,但我之所以沒有這麼做,原因是我對西藏的幾個關鍵問題還沒有形成明晰透徹的認識。後來,我又讀到徐明旭的著作《虔誠與陰謀》。他在書中刻意忽略以達賴喇嘛為領袖的噶廈政府在西藏大地上的消失,而且無視十萬藏人流亡印度半個世紀之久的悲慘命運。他更是揣著對藏傳佛教偉大哲學的道聽塗説來肢解西藏的文明。作為一個從上海來到拉薩的漢人,他那毫無陽剛之氣的身體由於無法適應西藏雄闊壯美的水土從而使他對那片藏人的家園充滿了刻骨的蔑視與仇恨。
一種透骨的寒冷,催生了我的憤怒。我覺得像李敖和徐明旭這樣的文人,其內心中沒有一絲一毫的人性的溫暖,有的只是刻薄和陰毒,是自私自大和虛妄無知。他們不顧自己的言論是多麼違反邏輯,但對西藏的惡毒指責卻滔滔不絕。顯然,王力雄先生則是一位宅心仁厚的學者,他能從藏人穿袍子和種地這樣的生活細節體諒西藏人在那種惡劣環境中生存的智慧。而我尤其需要指出的是,西藏人的智慧解決了一個實際而根本的問題,即人口增長的問題。由於眾多男女出家為僧尼(這種宗教現象讓許多持有生產力決定論的漢人找到了詬病西藏的藉口),因而抑制了人口的增長。這使西藏人在那片貧瘠的高原上不會因人口過剩而產生與自然的危機。佛教在這裏非常人道地解決了人口增長問題,而中國人直到現在,使用的竟然是非人道的絕育手術。或許,只有這個擁有長久閹宦史的國家才會想出如此奇妙的絕招。
我們絕大數漢人連最後一點常識與同情心都沒有了,還談什麼良知。
在三月十四日拉薩騷亂之前,我曾遊歷了西藏的許多地區,並在一個藏人的高山牧場生活了整整一年。在德格縣城,有一位名叫丹珠的老阿爸把我當成了他的兒子。在那個名叫戈麥高地的牧場上,人們把我當成了他們的親人。是的,藏人從來不把我看成是個外人。當我提出要去閉關中心看一看五位閉關五年的瑜珈師時,印南寺的堪布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請求(這是從未有過的一次特例)。因此,我才平生第一次得以親見瑜珈師的神秘面容。西藏瑜珈師的閉關苦修,完全超越了人體極限。正是因為這種超越,瑜珈師才能擺脫世俗、愚鈍的心靈而獲致精神世界的自由。僅從肉體的意義而言,瑜珈師的超越已經令人瞠目結舌。當時,正是冬天,我穿著羽絨服走進閉關中心,而那五位瑜珈師僅穿著單薄的袈裟,仿佛冬天的寒冷與他們的肉體絕緣了一般。也許,他們已經修成了拙火定。拙火定是一種修行的法門,它能使瑜珈師的身體產生一種熱能。據說,在離德格縣城不遠的八蚌寺,每年冬天都要舉行一場拙火定的考試。瑜伽師們坐在冰面上,身披浸濕的羊毛毯,用自身熱能將羊毛毯烤幹。
殖民地,軍閥,大獨裁者,大清洗,民族乃至種族的大融合,自由派與保守派的鬥爭,頻繁的內戰,共產主義、科學與迷信的混雜,信仰與原始巫術的共存……這一切,是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人們與拉美人共同擁有的人類渣滓。拉丁美洲的百年孤獨,也是中國的百年孤獨,同樣也是西藏的百年孤獨。我們和拉丁美洲人民一樣,追尋「一個新的、真正的理想王國,在那裏沒有人能決定他人的生活或死亡的方式,愛情將變為現實,幸福將成為可能;在那裏,那些註定要忍受百年孤獨的民族,將最終也是永遠得到再次在世界上生存的機會」。加布列爾•加西亞•馬奎斯(Gabriel García Márquez)如是說。
正是基於這樣一種追求,《西藏流浪記》第七卷「寓言書」,實現了我從美國BEAT一代向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轉向,同時,也完成了我從法國新小說派向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轉向。
在此之後,我寫作了《西藏紅羊皮書》(它先於我的處女作《西藏流浪記》出版面世)中一系列魔幻現實主義的故事。
在小說中,我將希望寄託在格桑喇嘛的身上。我在塑造一位智者的形象。這位智者能夠讓漢藏兩個民族趨向和解,他也能夠為西藏找到自由,當然,他是一位非暴力的倡導者。
目前,十四世達賴喇嘛倡行多年的不求獨立只求自治的「中間路線」遭遇了失敗。這是令人痛心的失敗。幾乎所有具有遠見卓識的漢族和藏族的知識份子都在擔憂,一旦十四世達賴喇嘛圓寂,西藏局勢就會失控,最終將導致流血衝突。這個前景對於漢藏兩族人民來說,都是一場災難。
但我相信西藏人的智慧。
「您知道,」拿破崙曾對法國作曲家兼政治家逢塔諾說,「世界上我最欣賞的是什麼?是以無力之力來創立某種事情。世上只有兩種力量,即軍刀和智慧。久而久之,軍刀終究會被智慧所戰勝。」
我相信西藏人的智慧終將戰勝軍刀,因為藏傳佛教就是一種以無力之力來創立某種事情的的智慧。
我也相信,西藏人的智慧終將為整個人類帶來福祉。
正是在這個意義上,我要在小說(同樣是以無力之力來創立某種東西)中,讓具體的國家和民族(西藏以及西藏的一切,只是一種符號)消失,因為我只想道出人類。
二○○九年八月十三日於北京
──本文為柴春芽最新小說《祖母阿依瑪第七伏藏書》之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