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的定義為何?有誰真正存在過?
貼上了小說最終回,他有點失望地關掉視窗。往後方的座椅一躺,點燃隨手拿起的香菸,深深吸了一口。兩手往後交叉撐住頭,凝視著天花板,陷入近乎冥思的狀態......
在香港小說網發表這篇作品時,也是同等失落吧?更早之前呢?
為什麼真相這麼難以了解?
他又深吸了一口菸,裊裊盤昇的迷惘,在碰到天花板之前,已然無蹤。闔起眼,有點累,在心裡問著自己:
「線索,很明顯了不是?」
死亡,不就是那麼一回事。
但是,「存在」呢?
那個黃昏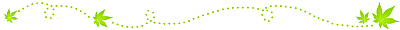
小五那一年?還是唸小六那時候?
每天,離開大夥的放學隊伍行列之後,愈是離家愈近,卡其服左側口袋裡那難以名狀的慌張,就越是像被灌滿氣的氣球,不斷地膨脹,不斷地膨脹,彷彿就要向外撐開爆裂。
有幾次,他試著打開口袋,裡頭除了更叫人心慌的虛無,啥都沒有。
「啥都沒呀...」闔上了袋口,他總是頹然垂下雙手滿滿的空盪,轉而踢踢路旁的小石子,拔拔幾根不知名的野草。那個遙遠的年紀,他只懂得如此處理自己的情緒。
每天,同一條必經的返家之路,那棟因建設公司倒閉便不再施工的廢棄大樓,此刻就離他不到五十公尺。那棟流浪犬的集中營。
幾年了?
廢工寮裡那隻魁武兇猛的惡犬,追他幾年了?
他不像其他的孩子,總有雙親或家人護送,他沒有。他只能自個兒想辦法應付。而他的方法,是快步狂衝過去,這法子,卻總是叫他失望的多。有時,他會幻想自己是頭獵豹,世上再沒有任何一種生物能追上他。自幾年前他們家搬到這鎮上後,家人幾乎不與外界寒喧互動,左鄰右舍的街坊自然識不得幾個,學校與家之間的路,他也只認得這條。
他只會走這條路。
「衝過去...今天一定行......」
他深吸了一大口氣,像在宣誓般用右手緊緊摀著心口,眼睛小心翼翼地四處掃視,緩緩輕移腳步,四十六公尺...四十五公尺......四十四公尺.........
三十五公尺...三十四公尺......三十三公尺.........
他雙手緊緊握成拳狀,不知從何處拔來的草仍渾然不覺抓在手裏:「那頭怪獸呢?」
驀地,右眼餘光掃到一團黑色陰影,正快速自後方朝自己逼近,他拔起腿來,不顧三七二十一死命地往家的方向跑。呼嘯過的風聲,身後逼近的低鳴,轉眼間,全具體化貼在腳下。那隻大黑狗咬住了他的卡其褲褲腳狂吼狂甩,他幾乎在同時間就失去了平衡,小小身形往前撲去,跌進一叢廢棄的工材裏。
黑狗咬了他的腳,咬了他的手,咬了他的身軀......天曉得那頭怪獸究竟想在他身上留下多少傷痕?
他下意識裏不斷地揮舞著手中的草,他那唯一的武器。
也不知過了多久,一聲淒厲的慘叫,像夕陽映下的血紅,傳入他的耳,灑遍他的臉,他甚至還能感受到日光餘暉的溫熱。然後,四肢的知覺回來了,聽覺回復了,視覺也從漫無邊際的空洞,凝聚成一個點。一個大黑點。
那黑點在地上扭動,一根生鏽的鋼筋橫生生自牠左胸口插入,至右後背穿出,與那黑點在黃沙土上,形成一幅極詭異的畫面。
「十字架!」他爬起身,收出右手,指向地上那團扭動,大聲狂喊。
那黑點似乎仍想努力掙脫那截貫穿牠身軀的異物,卻越是掙扎,越是深陷,鋼筋的一頭狠狠地插入黃土裏,牠嗚咽著以插入土裏的鋼筋為圓點,在地上劃起一圈又一圈的血痕。
他冷冷地看著,嘴角微微仰起一道淺淺的弧線......
終點或起點?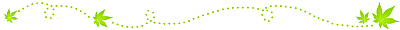
他又點燃一根菸,習慣性地深吸一口:「是從那時候開始的嗎?還是更早?」
煙霧往天花板上盤旋而去,他坐起身,打開右手邊置物盒最底層,拿出一付算命紙牌,把玩了起來。
冥冥中既定的命運?抑是無法捉摸的機會?
那天下午,他蹲坐在那團黑影旁,雙眼直直冷冷地盯著,直至那團蠕動在最後抖動了幾下,卡其服左口袋裡的慌張,也隨著散去了蹤跡。黃昏的餘暉籠罩著他,硬是把他蒼白的小臉烙個通紅。他立起身,往地上那團已靜止的恐懼慢慢趨近,隨即用雙腳不停地狂踢:
「去你媽的!去你媽的!去你媽的......」
隔著一雙紅透的布鞋,腳尖傳來逐漸的僵硬。他跨出右腳,踩住那團無聲的冰冷,雙手抓住鋼筋的一頭,使勁一拔,隨手丟進了廢工寮裏......
那時是怎麼回到家的呢?
他忘了。
命運的紙牌,正對照著一張「新的旅程」。
他把紙牌往桌上一扔,站起身子往窗旁踱去。拉上百葉窗,打開窗戶,外頭陽光普照。行道樹下的草皮有整群的麻雀吱吱喳喳著,好不熱鬧。循著視線,一個約莫十六、七歲的女孩,正牽著一頭馬爾濟斯晃過他的眼眸。
他深吸了一口菸,往窗外吐出,唇邊浮現一絲熟悉的弧線,似有若無地,往那少女離去的方向,悄悄揚起。
「終點?」他心裡自問自答著。
「當然不是,那只是另一個新型式的起點。」
雙子風 2007/02/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