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間關還鄉,一路上看白色的芒草開花。
在火車上這樣張望,心裡正有一種歲月悠悠的沉鬱,壓在那裡,不由分說。從前也有過這種感覺,這種類似的情緒吧,又彷彿未必。我默默獨坐在那裡,一向就是這樣默默,然而是惘然的,看車窗外白芒花閃過,不斷閃過,不知道這其中是否有什麼道理。起先僅僅如此,花在與我視線平行的小丘上,英英雪雪,迅速來去,或者在遠處山坡,如成群無數的綿羊,車聲不斷起落,羊群和平低頭。我的確注意到這一路上的白芒花,都垂垂蕤蕤,是因為小雨淋過的關係嗎?是因為小雨時下時停的關係,在這靠海的山地裡,火車以催眠的節奏向南奔馳,我坐著,眼睛必然是無神的,兩肩微微痠痛,心裡不一定想著什麼。沉鬱。十一月。
又是十一月。十一月的花,這豈不正是此生不斷,反覆來襲的,熟悉,令人動心的白芒花嗎?像夢魘,但它是美麗的夢魘,美麗而哀愁。起初它一定是美麗而哀愁的,當我們醉心美麗而不太知道什麼是哀愁的時候。終於有一天那一切都逐漸淡漠,甚至整個褪去,也不是美麗,也不是哀愁。只不過因為它,和一些類似的意象,竟不斷為我反覆著一些類似的情緒來襲,我就只能以為它是夢魘了。這時我斜斜靠著座椅,看它一簇一簇在潮溼的山坡飛逝,忽遠忽近,低著頭。似乎並沒有風,但不知道有沒有雨。這時我還斜靠座椅,發覺它逝去的速度卻緩下來了。不是花逝去的速度緩下,是火車預備進站。於是,火車越來越慢,進入有白色柵欄的小站,停下。柵欄外也長滿開花的白芒。這時,我看到柵欄這邊有一個小池塘,水面漣影瀰漫,是因為到處下著小雨,滴滴落在這無風的山地,打落開花的白芒。這時我竟能默默注視它,一朵,兩朵,三朵,數不完了。我本來不特別想什麼。於是我閉上眼睛,想到母親。
母親已經病了很久,而且愈來愈不好。這麼多年了,我已經習慣於午夜就寢以前想她,坐在燈前,對著書籍或文稿,忽然就想到病了的母親。對著那些平時作息不可或無的書稿之類的東西,忽然看不見那些東西了,眼前只剩一片迷茫,好像是空虛,母親的面容和聲音向我呈現,寧靜超然,沒有特別什麼樣的表情,那麼沉著,安詳。坐在燈前,有時我還能感受到她手掌的溫度,就像小時候發燒躺在榻榻米上昏睡,只要有點知覺,就希望母親來,靠近被褥坐下,伸手來我額頭探體溫。起初她的掌心是涼的,大概非常焦慮,等我慢慢退燒,她的掌心就變成溫暖的,撫在我醒轉的眉目之間,很舒服,很安全。這些年來,每當我午夜想念,在燈前,若是感受到母親的手探觸了我的額頭,臉頰,或者肩和背和手臂,那手心總是溫暖的。母親病了,我更不應該生病。
在這樣一個細雨的午後,相當遠的山地火車站裡,靠著斜斜的座椅,不免,我詫異地問自己:「為什麼呢?」火車又慢慢開動了,駛離那小站。我想我是明白的,為什麼呢?曾經在很遙遠遙遠的歲月裡,模糊泛黃的年代,應該就是那麼久以前的吧,在秀姑巒溪轉彎長流過的愚騃的大地,向東是大山,向西是大山,我猶記得熱天裡和母親在灰土小路裡蹀躞趕路。
知了聲在樹林裡聚響,路旁遠近都是兀自將開放的挺直的白芒花,我們偶爾停步休息,在一棵高大闊葉的喬木下,對著山坡下的樹林喘氣。母親為我擦汗,拿毛巾在我面前搖著搧風,給我水喝,給我餅乾和涼糖,然後她自己擦汗。這一切山坡下的白芒花仲長了脖子在看,山坡上的白芒花也遠遠俯視,點頭嘆息。知了持續在四處鼓噪。山嶺拔高,而藍天比山高,小朵白雲浮過,但陽光猛烈,晒在參差雜亂的各種樹木上。「為什麼呢?」我記憶完整。有一天近午,我們沿路走到一開闊的彎道,左邊是林投樹和一些矮竹,姑婆葉叢,右邊陡坡直落,視野迢遠,可以看見一條淤淺的河流,旁邊沙磧上堆滿山洪暴發時自高山沖來的石頭,更遠似乎還有茅草小屋和農作的田園,在錯落的檳榔和麵包樹間。那時忽然從東邊山脈缺口,傳來飛機引擎劃破縱谷的聲音,母親帶我滾下右邊的山坡,躲進雜樹叢生的凹地。我們聽到飛機隨意掃射的聲音,夾在推進器沉悶的巨響裡,竟然感覺它漸漸飛近我們上空了。母親把我用力向下推,滾進凹地底下,抱住我將我整個人壓在下面。我毫不猶豫地伏在那裡。我明白,我當然是很明白的,她想用她的身體作屏障,這樣掩護我;即使飛機掃射,也只能打到她,打不到壓在下面的兒子。原來她是這樣想的,我知道了。飛機從我們頭頂上喧譁越過,向開闊的河流區域航去,繞一大圈,聲音小了,遠了,一定是回海上去了。母親把我抱起來,幫我擦汗,把衣服彈乾淨,讓我坐好,然後她清理她自己,一邊小聲安慰我。她的面容和聲音寧靜超然。我注意到山頂俯身來看的,又是一些欣悅的白芒花,而坡底更有許多白芒花,也都在前後搖動,興高采烈地看我們。好風緩緩吹過,知了乍停而續,又停了。我聽見四處鳥聲,細碎嚶嚀,短暫卻似永恆,知了復起,把亭午的太陽光吵得更烈了。
現在我閉上眼睛休息,但始終是不平靜的,在心裡,惦記太多,翻動鼓盪的思維,使我不能真正休息。火車的節奏在變化,過完收割後的水田,蔥蘢的菜園,魚池,正在過鐵橋。是這樣的一種旅程,一種倦怠的旅程,因為憂慮,不安,焦躁。這時已無所謂哀愁,已超越了哀愁,也似乎沒有什麼美麗,沒有什麼一定要使你為它醉心的美麗。火車在鑽山洞,聲音忽然加強。本來睜不大的眼睛這時更瞇成線了。
又是十一月。我都記得,記得詳細。
去年的十一月也這樣嗎?好像不是這樣的。
但我確實記得去年十一月的白芒花,在同一條火車道左右,如此盛開,小山遠近,丘陵高下,在更遠更遠的平埔野地裡,廣泛散開,彷彿是不斷繁殖著的,我記憶裡的白芒花,愛的見證,信念,和毅力--一種無窮盡的象徵,永不止息的啟示。然而去年十一月的白芒花更明更亮,更燦爛,這些我也都知道,知道花挺直地搖著晃著,毫不羞澀,也沒有任何愧悔。甚至當火車從山洞裡轟一聲鑽出來的時候,向左邊看,就在防風林外,一片潔白的沙灘上,白芒花也開著,朝碧藍的大洋,永不休息的浪,它開著,在風裡。我知道它更明更亮更燦爛,曾經就是如此,猶似新雪,在我曾經的旅程。
而那些是回不來了。那些以及更久更久以前的白芒花,在山谷,河床,在丘陵上,漫山遍野,清潔而且沒有顧忌,如此活潑,自由,好奇。那些是回不來了的,縱使我招呼它,央求它,閉起眼睛想像往昔何嘗不如同今朝這麼確切明白?我知道這並不是真的。那些已經逝去,縱使我都記得,記得詳細。甚至去年十一月的白芒花也枯槁,萎落,而今年間關返鄉路上看到的,裛落細雨裡,不斷為我重複著一些類似的情緒來襲。 -
-定稿於一九九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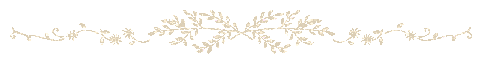
文章來源網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