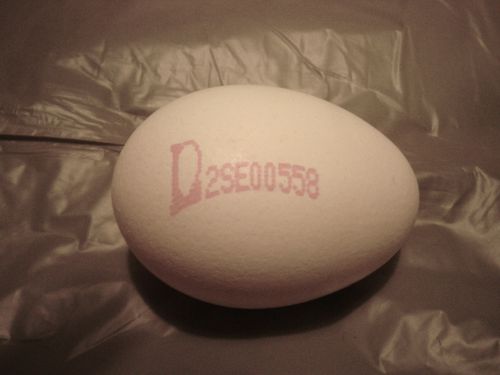荷蘭篇/棄圩田復水道 還地於河與自然共存
聯合報/記者陳乃綾/荷蘭採訪
 |
| 荷蘭蘭斯塔德地區,雖是政治、經濟發展重要地帶,但郊區仍保有田園景象。 記者陳正興/攝影 |
|
走在荷蘭南方知名觀光景點「小孩堤防」上,放眼望去,十八座巨大的美麗風車佇立轉動。荷蘭號稱風車之國,但多數人不知道,荷蘭風車作何用途?
荷蘭全國三分之一土地低於海平面,為增加土地生存空間,荷蘭人過去築堤控制河道流向,在原本是河道的區域上,建起眾多風車,利用風能抽乾河水,形成可供居住和農用的「圩田(polder)」。
全荷蘭約有三千處大小圩田,顯見荷蘭人「與水爭地」歷史悠久,歐洲有句諺語:「上帝創造世界,荷蘭人創造荷蘭。」
然而,近年氣候劇烈變遷,低漥地面臨海平面上升與河水暴漲威脅。荷蘭的空間規畫與河海管理觀念,已從過去「人定勝天、與水爭地」轉為「與自然共存」。
荷蘭「三角洲委員會」是負責治水的獨立機構,資深顧問艾爾凡(J. van Alphen)說,為避免洪災,政府過去選擇在河岸築堤擋水打造圩田,創造新的生存空間;但河川日益沉積導致水位升高,河堤也越築越高,多處河堤已出現潰堤危機。
 |
| 從與水爭地到與水共生,荷蘭近年往水面上發展居住空間。三座足球造型的實驗性「漂浮屋」,是鹿特丹南方之角新地標。 記者陳正興/攝影 |
|
花了十年 與民溝通
三角洲委員會兩千年提出「還地於河計畫」,放棄部分人工造陸的圩田,恢復河水原來水道,計畫總長達三百多公里。
為了瞭解還地於河計畫,隨行採訪的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邀請他過去在聯合國水環境教育學院擔任客座教授時的老同事周仰效教授,帶領聯合報系採訪團隊,探訪荷蘭南方的比斯堡國家公園。這塊公園旁,就緊鄰一塊「圩田」。
在圩田與萊茵河支流瓦爾河之間的大堤上往內看,可見一道新堤防正興建中,堤上還有三座水閘門。這就是荷蘭政府兩千年啟動的「還地於河」計畫地點之一。
周仰效說,新堤竣工啟用後,政府將打掉舊堤,讓堤防向後推移,使河道加寬、水位隨之下降;堤防水閘門則在洪汛期間打開,洪水流入可以滯洪的圩田,紓解對下游的威脅。
艾爾凡說,為順利執行還地於河,荷政府花十年時間與當地居民溝通,再以略高於市價價格徵收土地並撤離居民與農舍,加上工程款共投入廿億歐元。這些新堤防工程明年全數完工後,新的萊茵河防洪計畫即將啟用。
三角洲委員會做的不只這些。北海兇猛海水在風暴期間經常引起海水倒灌,導致低窪地區澇災,荷蘭一九五○年陸續啟動三角洲工程,在海岸構築堤壩和出海口的大型水閘道,阻擋北海海水對陸地的騷擾。
 |
| 三角洲工程。 記者陳正興/攝影 |
|
三角洲 護蘭斯塔德
荷蘭中西部由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烏特列支四大城市環繞圍成的區域,稱做「蘭斯塔德(Randstad)」。三角洲工程不僅讓荷蘭居民不再懼怕海水倒灌,也讓荷蘭境內城市縱橫交錯的運河維持穩定水位。三角洲工程,可說是保護蘭斯塔德精華地區無憂發展的大功臣。
從與水爭地到還地於河,荷蘭善於因應環境變遷進行調適,讓土地利用達到最適合生活的狀態,「把空間還給自然、把時間還給人民」。
隨行採訪的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說,台灣國土面臨地盤下陷、洪災問題,與荷蘭低地非常類似,荷蘭花十年完成還地於河,以更高思維看待國土規畫;反觀台灣,從八年八百億到六年六百億,治水卻只停留在工程手段,也無法確保不再淹水。
李鴻源說,台灣不需完全複製荷蘭方法,但如何重新規畫土地、與自然和諧共存,整體邏輯應向荷蘭學習。
【2014/08/11 】
荷蘭篇/城市規劃重溝通 甚至徵詢遊民
聯合報/記者陳乃綾/荷蘭採訪
 |
| 阿姆斯特丹市內的運河縱橫交錯。 記者陳正興/攝影 |
|
荷蘭不僅是規畫之國,也是共識之國。
荷蘭不僅是規畫之國,也是共識之國。
為瞭解阿姆斯特丹市如何城市規畫,採訪團隊拜訪市政府空間規畫副處長海默(Z. Hemel)。海默則開門見山說:「談規劃之前,要先談共識」,政府在規畫前,需花很多時間蒐集市民對城市的看法,務求「最大化」市民參與。
城市結構願景計畫成型之前,政府還舉辦公開的展覽和工作坊,讓市民理解城市目前面臨的問題,並有機會暢談對城市的願景。
海默指出,市民發表看法時,不是只「抱怨東、抱怨西」,而會提出有趣的草根觀點,反而打開官員的視角,有利政府做出「有感」的規畫。
「我們甚至會徵詢遊民的意見,因為長期在阿姆斯特丹街上生活的四千名遊民,知道哪裡可獲得食物、哪裡有庇護所,是最了解城市角落的族群。」海默說。
「政府常以專家自居,從高角度往下看、忽略『群眾的集體智慧』。」海默認為,整座城市就是一座可自我運作的大腦,群眾的多樣性,才是成就有機城市的關鍵。
隨行採訪的內政部前部長李鴻源說,荷蘭政府推動政策,如還地於河政策,三角洲委員會花了多年時間與居民溝通,務求達成共識,以確保政策的可行性與永續性。
「台灣政府與社會的溝通不到位,許多公聽會、說明會只是依法行政、便宜行事,導致許多民眾不理解政策邏輯而發動抗爭,許多政策經過多年都無法落實」,李鴻源強調,政府如何與民眾達成「夥伴關係」,是台灣政府官員必修的功課。
重視溝通的荷蘭政府,形成特殊的共識文化。荷蘭政府以「溝通之鑰」打開政策執行的大門,值得台灣借鏡。
【2014/08/11 】
荷蘭篇/保護綠心 地方畫紅線區不開發
聯合報/記者陳乃綾/荷蘭採訪
四月是「荷蘭國花」鬱金香盛開的季節,搭乘火車從荷蘭萊登市旅行到海牙市,十二分鐘車程,多數時刻窗外風景是一望無際的綠地與鬱金香花田。
位置相近的兩個城鎮,通常會逐漸開發,連成一片大都會區,一如台灣西部平原的都市化與郊區化開發。但在荷蘭,政府有計畫保護城市之間的綠地,避免都市過度擴張。
荷蘭為什麼要保護綠地?「因為荷蘭人重視生活品質。」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資深空間規畫師巴倫(R. Berents)說,居住環境是否親近自然,是最重要的生活品質指標。「阿姆斯特丹的城市規畫原則,就是確保住在市中心的居民,騎腳踏車十五分鐘內,就可抵達市郊綠地親近自然、放鬆身心。」
荷蘭人「與自然共存」的基因,存在蘭斯塔德的心臟--「綠心(Green Heart)」。這片廣達四百平方公里的綠色開放空間,被荷蘭四大城市所圍繞。綠心內沒有商業大城,也沒有工業區,只有農田、畜牧場和森林。
台夫特大學建築與城市學系教授松納菲爾(W. Zonneveld)說,保護綠心,已成荷蘭國土規畫最基本價值,二千年初期中央政府曾要求各省政府畫下「紅線區地圖」,紅線內為可開發區,線外則不能蓋房子,以保持綠心的開放性。
不過,荷蘭也面臨人口增加、居住需求增多的壓力。為避免城市過度擴張,荷政府六○年代未雨綢繆推出「新鎮策略」,在靠近大城市的一塊土地創造出新城鎮,規畫住宅區,建造有花園、車庫的獨棟洋房社區,吸引擁有汽車、想住市郊的中產階級進駐「新鎮」。
在新鎮和大城之間,政府也確保「綠色緩衝區」。松納菲爾說,政府甚至會向私人買地種樹,為市民創造森林、湖區和小型農耕的休憩空間。
人口往郊區新市鎮移動,八○年代大城市市中心人口也相對減少。荷政府便推動「集約城市(Compact City)」目標,將大城市市中心閒置土地、舊廠房,改建活化成新住宅區,提高市中心的使用密度和居住率。
荷蘭基礎建設與環境部空間發展處副處長史諾肯(H. Snoeken)說,從新鎮到集約城市,荷政府採行的是「集中式分散」(concentrated deconcentration)策略--將可能擴散的人口和居住需求,有計畫性地「集中」在某些規畫好的區域,分散都市的人口壓力。
荷蘭中央、省、市三級政府都設有國土空間規畫的專業部門。中央政府內的基礎建設與環境部,二○一二年提出全新的國家空間計畫政策報告書,規定中央、省、市都需要有規畫出可達成「競爭力、交通便捷、適居、安全」四大目標的策略(Structure Vision)。
這份政策報告書並非政府獨立作業的成果。史諾肯說,政府附屬的智庫單位「荷蘭國家環境評估署」(PBL)經常對政策做出評估,荷蘭政府也常與學者交流;如組成共有八名空間規畫專業教授的顧問委員會,每年開兩次會,向政府提供建言。為了讓基礎建設、地景和建築規畫更具美感,政府也邀請知名的建築師、空間設計師組成顧問委員會。
此外,非政府組織NGO也荷蘭國土規畫上扮演重要角色。松納菲爾舉例,擁有七十萬名會員的「National Nature Trust(Natuurmonumenten)」,會員人數比任何政黨的黨員數都還多,故在荷蘭國土規劃上擁有廣大影響力。
當政府的建設規畫有破壞生態景觀之虞,NGO會集結出來抗爭,甚至告上法院。政府往往會採納NGO的意見,修正建設計畫。
松納菲爾舉例,阿姆斯特丹艾堡地區著名的水上漂浮住宅社區,在建造前,NGO擔心這項實驗性住宅計畫會破壞水岸生態;經多次溝通,政府從善如流,將環保生態、綠建築的概念納入漂浮住宅的開發計畫中。
「專家導覽員」李鴻源說,他觀察到,荷蘭的空間規畫不單是由政府由上而下埋頭苦幹,而是建立「知識網絡」,重視產官學合作,並與各種不同專業組織合作,這正是我國政府所缺乏的橫向專業交流。
 |
| 圖/聯合報提供 |
|
【2014/08/11 】
荷蘭篇/都更活化…改造鹿特丹 加值史基浦
聯合報/記者陳乃綾/荷蘭報導
 |
| 漂浮屋。 記者陳正興/攝影 |
|
全歐洲運量最大的海港與旅客數最多的空港,都位在荷蘭。鹿特丹港與史基浦機場,是荷蘭成為歐洲物流、人流的中心樞紐的重要門戶。這兩大歐洲門戶在九○年代分別啟動「南方之角」和「機場城市」兩大國家級計畫,成為荷蘭土地活絡規畫的「示範區」。
南方之角:舊港變新城
鹿特丹「南方之角(Kop van Zuid)」原是鹿特丹舊港區,因應日益增多的船運量,市政府和港務局一九九○年代聯手將港區移到四十公里外的海埔新生地,舊港區則拆除部分港務設施,在原來是關務機構、倉儲工廠的土地上開發新城鎮。
新馬斯河將鹿特丹南北區橫向隔開,北邊有交通建設和商業區,南邊則長期是藍領階級的住宅區。鹿特丹市政府城市計畫專案經理海寧(S. Geenen)說,活化南方之角舊港區、吸引中產階級入住,成為市政府平衡南北發展的武器。
鹿市政府首先建造知名的斜張橋「天鵝橋」,連接北區與南方之角,地鐵系統也穿過新馬斯河下與北區連結。基礎建設完成後,再將各政府機關先移到此區,展現政府「玩真的」決心。
接下來則鹿特丹市政府則啟動一連串都更計畫,新增五千戶住宅、設立辦公大樓和文化空間,成功將南方之角打造成適宜人居的「新市中心」。
 |
| 荷蘭阿姆斯特史基浦機場內的景觀。 記者陳正興/攝影 |
|
會議、物流加值 打造經濟廊道
二○一三年,超過五千萬名旅客進出史基浦機場,四十二萬架飛機在此起降,飛往歐洲各國的班機,大多都得在史基浦轉機。這不僅是地理位置造成的優勢,而是史基浦周邊航空會議轉運中心和物流中心帶來的加乘效應。
史基浦機場位於阿姆斯特丹市西南方郊區,有鐵路直達阿市和南邊的海牙市、鹿特丹市。九○年代機場公司決定打造機場城市,在機場旁設立「世貿中心」,做為會議轉運中心。
史基浦機場公司資深城市規劃師夏夫斯馬(M. Schaafsma)說,許多國際企業都喜歡在史基浦的世貿中心舉行會議,旅客一出境,拖著行李就能走到會議地點;會議結束,可選擇入住機場旅館,或直接搭機返國。如此方便高效的空間規畫,讓史基浦成為歐洲與全世界會議樞紐。
機場周邊的部分農地也被徵收,改造成物流轉運園區,許多國際大型企業都選擇在此設立物流中心集散貨物,如YAMAHA、波音公司、三菱汽車等。
夏夫斯馬說,史基浦機場正與阿姆斯特丹市政府合作,機場城市將與阿姆斯特丹南邊區域連結,形成一條「機場經濟走廊」,引進國際企業營運總部、產業研發中心、醫療中心、金融服務業、休閒產業等。夏夫斯馬說,期望未來這條走廊,可成為帶動荷蘭的經濟成長的經濟命脈。
【2014/08/11 】
荷蘭 綠色是最美的共識
特派記者陳乃綾/荷蘭報導
「整個城市就是一座自行運作的大腦,群眾多樣性,才是有機城市的關鍵。」
▲內政部前長李鴻源參訪荷蘭三角洲工程,對於荷蘭以多年耐性溝通,務求達成官民共識,省思台灣官員是否有「二、三年耐性,去跟大家面對面溝通」。udn tv/記者陳怡真、游家瑋製作
荷蘭全國三分之一土地低於海平面,過去為了增加生存空間,築堤控制河道、用風車抽乾河水,形成可居住農作的圩田。「與水爭地」的氣魄,讓歐洲諺語說「上帝創造世界,荷蘭人創造荷蘭」。
然而,為了因應氣候劇烈變遷,荷蘭三角洲委員會在2000年提出「還地於河計畫」,開始放棄部分人工造陸的圩田,恢復河水原來水道,總長達300多公里,把空間還給自然,避免河川繼續淤積水位攀高、不再讓河堤愈築愈高。
 |
| 三角洲工程恢復河水原來水道。 記者陳正興/攝影 |
|
改變從來不是簡單的事。負責執行計畫的三角洲委員會資深顧問艾爾凡(J. van Alphen)說,政府花了10年時間與居民溝通,再以略高於市價徵收土地,撤離居民與農舍,加上工程款共投入20億歐元(約台幣823億元)。這些新堤防工程明年全數完工後,新的萊茵河防洪計畫將啟用。
4大城環繞綠心
荷蘭中西部有片400平方公里的綠色開放空間,被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烏特列支等4大城市圍繞,這片稱為「綠心」的區域,沒有商業大城、工業區,只有農田、畜牧場和森林。
阿姆斯特丹市政府資深空間規畫師巴倫說,「城市規畫原則,是確保住在市中心的居民,騎腳踏車15分鐘內,就可抵達市郊綠地。」保護綠心,已成荷蘭國土規畫最基本價值。
 |
| 「綠心」只有農田、畜牧場和森林。記者陳正興/攝影 記者陳正興/攝影 |
|
 |
| 城市規畫原則是市中心居民騎單車15分鐘內可到市郊綠地。 記者陳正興/攝影 |
|
同樣為了紓解人口與居住需求壓力,荷蘭從上世紀中就展開城市規劃:包括「新鎮策略」未雨綢繆規畫大城市附近新住宅區;「綠色緩衝」確保新鎮與大城有樹林存在;「集約城市」將市中心閒置土地、舊廠房,改建活化成新住宅區。
9
徵詢遊民意見
阿姆斯特丹市府空間規畫副處長海默(Z. Hemel)說,「談規畫前,要先談共識」,政府花很多時間蒐集市民對城市的看法,務求「最大化」參與,包括聽取遊民的意見。他說,整座城市是一座可自我運作的大腦,群眾的多樣性,才是成就有機城市的關鍵。
另外,非政府組織「National Trust for Nature」,對於荷蘭國土規畫政策擁有廣大影響力,擁有70萬名會員,比任何政黨的黨員數都還多。當政府有破壞生態景觀之虞,NGO會集結抗爭。政府往往會因此修正建設計畫。
 |
| 荷蘭水上漂浮住宅區,人置身其中不僅感到與水共存的規畫美感,也具有日常生活感。 記者陳正興/攝影 |
|
【2014/08/11 】
名家觀察/三角洲工程 解決荷蘭水患
聯合報/李鴻源
荷蘭全國面積四萬平方公里,人口一仟柒佰萬,全境沒有一座山,大半的國土都低於海平面,最嚴重的地區低於海平面五公尺。因為位於萊茵河的出海口,加上北海的暴潮,淹水成了荷蘭千百年來揮之不去的夢魘。
從十二世紀開始,先民就開始了填海造陸的工程,荷蘭著名的風車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要將水從低地抽往地勢較高的河道,因其造型特殊,反成了荷蘭最著名的地標,也成了國家的象徵。為了執行此項艱鉅的任務,需要全民及各級政府同心協力,於是組織了水利會。整合、協調、對話的夥伴關係成了千百年來荷蘭政府運作的文化。就因為這獨特的文化,這一人口不多、資源缺乏、災害頻繁的小國能在十五世紀成了海上霸權,至今在歐洲仍扮演著舉足輕重的關鍵角色,更是世界上對外援助名列前茅的國家。
二次大戰後的一次大水,奪去了荷蘭一仟捌佰多條人命,此傷亡人數甚至超過二戰戰火的荼毒,於是他們開始策劃舉世著名的三角洲工程,用系列的防潮閘門、海堤、抽水設施將荷蘭的西部低地做了徹底的保護。這些鉅大工程的施工難度,在三四十年前是項幾乎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對海象、潮汐及河川水文水理的了解與掌握,現地施工技術之突破,都是史無前例的。於是他們投入了龐大經費從事水利相關的基礎研究,成立了數個至今仍舉世聞名的研究單位及學校。經過二三十年的努力,三角洲工程完成了,徹底解決了荷蘭的水患,同時練就一身工夫,成了世界上治水技術的主要輸出國。
開發中國家的學子及公務員絡繹於途,過去中國大陸每年約有超過百名的水利官員在荷蘭修習碩士學位,也曾是台灣省政府水利局及自來水公司培育人才的主要伙伴。於是透過教育,他們即可技巧地主導世界的水利議題及巿場。把一個危機轉化成轉機,進而變成商機,就是這個國家的生存之道。
自邁入二十一世紀,氣候變遷成了人類生存與否的最大挑戰,如何因應與調適,世界各國無不列為優先政策。荷蘭約在2003年即開始進行因應氣候變遷的相關政策的論證,從科學研究、産業轉型、組織改造、法令制定到國土規劃等各個不同面相切入。
首先定義何謂氣候變遷?為什麼引發氣候變遷?氣候變遷會對社會帶來多少衝擊?現有科技是否可消弭這些衝擊?要花多少錢來辦這些事?最後誰來執行此一艱鉅的工作?因為這政策的制定會影響到所有的土地使用標的及大部分人的生活,涉及各級政府的運作及法令的修訂。為了讓民眾能充分了解及意見表達,他們總共用了兩年時間,進行了將近四仟小時的對話,取得大方向的共識後,再進行細部的規劃。
政策的擬定需要專業的支撐,他們投入大量經費(在2004到2012年間共投資3.5億歐元折合約140 億台幣)整合全國各主要大學及科研單位,從事全面的研究及分析。再將研究成果與對話預案相互印證。於是分歧逐漸消弭,最終達成多贏的共同目標,然後再交由相關部會逐步落實。
因為氣候變遷,荷蘭必需承擔所有河萊茵河集水區增加的水量,河川的通洪能力已不是傳統的工程手段能解決的。因此他們的主要調適策略定位為與水共生(room for water),利用土地使用標的改變及都市設計的手段增加行水及貯水空間。包括35個子計劃,總預算23億歐元(約1000億台幣),預計2015年完成。除了將空間還給自然,增加河川的滯洪空間,降低鄰近城市的淹水風險外,同時涉及遷村、安置及地方政府財務等,結合沿岸城市的都市計劃,打造水岸空間。
我們去參訪了鹿特丹附近的一個案例,他們從八年前就開始規劃要拆掉Dorech 城附近萊茵河的一段堤防,將一大片在八O年代屯墾的牧場轉變成滯洪池。但這塊地上已有許多的農戶,剛開始配合意願不高,且意見相當分歧。他們共花了兩年的時間和農民對話,願意搬走的,政府協助他們在荷蘭東部取得土地,重建家園,不願意離開的,政府協助他們將房屋及牛棚建在土丘上,平時他們可如常的使用土地,但在洪泛期間仍有避災的空間,達到雙贏的目的。施工期間幾乎沒有抗爭,目前計劃已接近完工階段。
更值得一提是,荷蘭在積極面對氣候變遷挑戰的同時,同步成立一個跨國的三角洲聯盟(delta alliance),希望透過這一聯盟的運作,將荷蘭經驗輸出到世界各國,共同面對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敵人。同時也爭取他們在這一項目的發言權及主導權,當然背後有無其他商業考量,自然不在話下。
台灣和荷蘭一樣都是地狹人稠、資源缺乏的國家,也差不在同時開始規劃因應氣候變遷的政策,在三角洲聯盟草創之初,他們對台灣表達濃厚的興趣,因為台灣在水利相關科技的能力,是亞洲國家中的佼佼者,而且台灣有許多荷蘭所沒有的挑戰及技術。
希望透過這一機制,除了一方面解決台灣本身的問題外,更能進而能將技術輸出,協助其他亞洲國家建立他們政府相關的職能(capacity building),解決他們自己的問題。我很熱心的邀請荷方主要的負責人,拜訪當時藍綠政府的高層官員,我們也表達高度興趣,可惜十多年來研討會辦了不少,知名專家絡繹於途,但主要關鍵工作一直沒有落實,錯失一個可以積極參與的國際平台,也失去一個新觀念引進的暢通管道。
每年三角洲聯盟都會在世界各地舉辦各式各樣的研討會,也都會邀請我這位老朋友參加,但我一直都不敢與會,因為我無法向他們解釋為何台灣當初的承諾都沒有兌現。看著人家有計劃有節奏全方位地在面對他們的問題,而且已逐步落實。十多年下來荷蘭的政府改組了,相關法令修訂了,國土計劃的觀念改變了,甚至連學校的學程都不一樣了。我們卻還在原地踏步,還在用最傳統的思維方式在面對一個未知的巨大變局。其心情豈是徒呼負負四個字可形容。
另外荷蘭的公民參與全民對話是此政策能落實的最大關鍵,我不禁要問透過兩年的對話來弭平爭議尋求共識,我們的政治人物及媒體是否有這樣的耐心及決心?不要羨慕荷蘭的成就,而是要學習人家形成決策的過程及真正民主精神的落實。在面對氣候變遷這部份我們已落後了十年,我們還有多少十年可浪費?當下一波災難來臨時,我們真的準備好了嗎?醒醒吧,台灣!
【2014/08/11 】
採訪側記/規畫之國荷蘭 也是共識之國
聯合報/記者陳乃綾/荷蘭採訪
這次赴荷蘭採訪,訪談了十五位國土規畫、城市設計、水文治理、都市更新等各領域專家。我發現,荷蘭人可能是全世界最喜歡、也最擅長規畫的族群。
為了防止都市擴散到郊區而侵蝕「綠心」,荷蘭人想出「新鎮」政策來紓緩人口增加的壓力;為了避免海水在風災期間倒灌,荷蘭人甚至築起大堤,把內海封起來,讓源源不絕的河水持續淡化這座「人工堰塞湖」,湖水也可做為民生水源。
荷蘭人不只是務實規畫,他們做的是「有遠見的規畫」。譬如國土規畫,現在的荷蘭人,已預先想好三、四十年內可能發生的氣候、人口、經濟、社會變化,並將這些因素納入考量,擘畫出二○五○年的荷蘭願景。因為荷蘭人認為,每一項政策,不僅得「現在可行」,還必須是「未來永續」。
走訪阿姆斯特丹、海牙、鹿特丹三個西部大城市,我們看見的是工整的街道、設計完善的腳踏車道、豐富的生活機能和供居民休憩的大片綠地。荷蘭人的規畫痕跡隨處可見。
這趟採訪了解荷蘭人的規畫歷程、走訪規畫後的成果。但我發現,台灣與荷蘭雖然在土地面積、人口數量都有相似性,但畢竟歷史、文化、社會背景大異其趣,荷蘭許多規畫都有其時空環境因素。而台灣這座島嶼內,有些事已經「覆水難收」,恐怕只能「砍掉重練」。
我反覆在心中自問--台灣該如何「複製」荷蘭經驗?
訪談過程中,無論官員、教授或建築師,每位受訪者不約而同強調溝通和共識的重要性。荷蘭過去與水爭地,早在十三世紀就成立地方性的「水利委員會(water boards)」,由居民共同組成抵抗洪災、圍湖造田。這種互信、互助、擁有相同目標並共享成果的歷史傳統,流傳至今便成為荷蘭人DNA中特殊的共識文化。
一項政策當然需要由精密的科學研究支撐,才能進行評估、設計、規畫,但若無法在社群中達成共識,推行的困難會大大增加。回過頭來看台灣,舉凡苗栗大埔、桃園航空城、大巨蛋、美麗灣度假村等開發案爭議,先不論政策設計是否有瑕疵,政府在推行政策過程溝通不足、無法傾聽民意,是事實。
當政府和社群間缺乏雙向的對話溝通和彼此妥協,施政就成為人民與政府的零和遊戲,最後只會兩敗俱傷。
既然國土規劃的成果無法複製,就讓我們學習荷蘭人規畫背後的「共識精神」吧!在規畫之前充分的與人民溝通,因應大眾合理的需求而修正政策,才是讓政策可長可久、永續的方法。
【2014/08/11 】
slideshow/借鏡荷蘭
【聯合新聞網】
【2014/08/11 】


 本城市首頁
本城市首頁



























 在瑞典,食品安全不僅是來自政府嚴格的把關,還來自慢食文化、從小做起的食育,以及保護環境意識的高漲,這些相互關連的飲食觀念,成為瑞典人尊重生活的態度。
在瑞典,食品安全不僅是來自政府嚴格的把關,還來自慢食文化、從小做起的食育,以及保護環境意識的高漲,這些相互關連的飲食觀念,成為瑞典人尊重生活的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