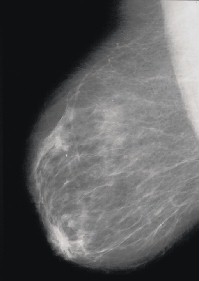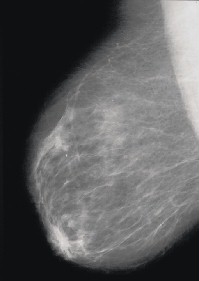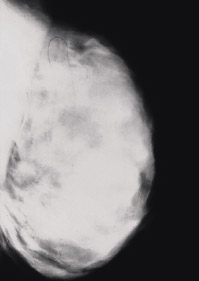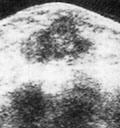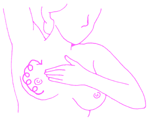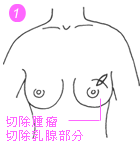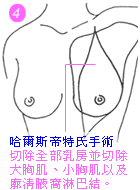| 【聯合報/文/福汐】 大官被這個村子遺棄了,被還活著和看上去還健康的村民們遺棄了。他的妻子說:人家在路上看到他,就用手捂著鼻子,有的小孩害怕了,就大聲哭叫。將來,他死了,還不知有沒有人肯來埋他?上個月,想送他到醫院,踩三輪車的人怎麼都不肯來,給多少錢都不來…… 虛弱的大官淡淡地靠在木門邊,望著黃昏時漸漸暗下去的院子。院子裡有頹敗了的豬圈,有擱置已久的農具和滿地的玉米棒子。晚歸的雞伸長了脖子在地上寂寞走過。 已經有一個多月了,大官不敢走出家門,去看看他曾經耕種過的田野,看看那個凌亂污濁然而被綠樹圍繞的水潭,還有從村裡的小路上走過的老人和小孩。 他身後的門框上是一幅殘缺的對聯,對聯的橫批寫著:美滿幸福。 大官「美滿幸福」的家包括他的妻子和一兒一女,還有的就是那褪了色的磚房和屋裡的一架黑白小電視。 「已經有半個月沒給他吃藥了。」大官也感染了愛滋病毒的妻子說起來就發愁,「家裡沒錢,再說,醫生一聽說你得的是這個病,連看都不給看,叫你趕緊走。到醫院去只敢說是感冒了,開點發燒藥。現在,連發燒藥也買不起,隨他去吧,反正也不管用。」 大官一家的生活,從九一年到九六年靠賣血,九六年以後靠賣豆腐;今年年初大官發病以後,沒人再敢買他做的豆腐,一家人就靠借錢過日子。 大官被這個村子遺棄了,被還活著和看上去還健康的村民們遺棄了。他的妻子說:人家在路上看到他,就用手捂著鼻子,有的小孩害怕了,就大聲哭叫。將來,他死了,還不知有沒有人肯來埋他?上個月,想送他到醫院,踩三輪車的人怎麼都不肯來,給多少錢都不來。 這個村子,村子裡所有的村民,有病的,沒病的,其實都已經被遺棄了,被這個社會,被還未感染上愛滋病的人們所遺棄。 「村裡種的西瓜賣不出去,糧食也很久沒有人來收了。」大官的妻子說。 六年前,愛滋病已經在河南被發現,到現在,六年過去了,這個村子還沒有等來一個政府官員或者是醫療人員,位於一公里之外的人民醫院也沒有教會村民蚊子是否會傳染愛滋病。小小的村子裡,這一年來已經死了二十多位青壯年。早先死去的那些人並不知道為什麼死去。那時候,這種病在村裡被稱為「怪病」或者是「無名熱」。村裡的人們到今年才知道這叫「愛滋病」。 而等待死亡的大官小聲而怯懦地問:跟孩子一桌吃飯會不會傳給他? 大官已經數不清他賣過幾次血,他一共有三本「供血證」,分別用三個不同的名字,為的是能一日多賣。「父親得肺病的那年,趕得早的話,一天就跑三個地方,帶著孩子他媽。」大官說。 大官的「供血證」是紅色的,像政府部門用的獎勵證書,封面印著「衛生部監製」。裡面的簽發單位處蓋著紅印章,紅印章的字跡是「睢縣紅十字血站」。大官賣過血的地方有人民醫院、防疫站、縣醫院、市醫院……。 在只剩下回憶的生活裡,大官還依稀記得那些陽光明媚的早晨。他說:「太陽一出來,我們就動身,馬路上都是人,本村的也有,外村的也有,都到馬路上去等班車,去晚了就擠不上。」 那條兩旁佈滿防風林的馬路通向外面的世界,通向更大的城市,通向商丘、開封、鄭州。那也是一條通向富裕生活的道路,那幾年,那個縣城的宣傳口號是:要致富,「獻」血去。誰會知道那是一條兇險獰猛的不歸路,迎接他們的,是因陋就簡的血站,病原流竄的針筒。 比起大官,妻子的回憶令人心酸,她說:婆婆死的時候,沒有錢辦喪事,大官幾個兄弟就趕去開封賣,連出嫁了的姐姐也幫著去賣,他們現在查出來都有……。 大官對門的鄰居樹村有三個孩子,孩子的媽三個月前已經死了。三十三歲的樹村長得高大結實,看上去很健康,他還沒有做過HIV檢查,將來也不想去,他說:查出來,又能怎樣?還不是一樣等死,大家聽說你得了這種「髒病」,連門都不來串。 樹村喜歡笑,一說話就張嘴笑,同時也靦腆地低下頭,抽口菸。樹村在講述他妻子去世時也是這種表情。當初,妻子的脖子上長了一些斑塊,一幹活就累,她懷疑自己也得了這種病,那些死了的病人也有過這種症狀。樹村讓她去鄭州檢查,她沒有去,自己一個人偷偷喝了一瓶農藥。「她怕拖累了家人,看病太貴,檢查一次要花一百塊錢,還得要路費,家裡沒有錢,那點錢供孩子讀書都不夠。」樹村依然是微笑地說著,周圍站著的十幾個村民靜靜聽著,沒有一個人哭,除了我,從心底裡哭。 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已經沒有了眼淚,就像斷流了的母親河?從什麼時候開始,人們的心靈已經疲憊而且荒蕪如沙漠,彷彿再也盼不到一滴雨水,只求在更廣闊的沙漠裡死去,就像已經乾涸了的河床,它所能期望的除了上天還是上天? 天晚了,大官的孩子還沒有回來,妻子把他送到很遠的學校去讀書。「原來是在村裡讀的,聽說他爸爸得病了,老師就不讓他再去,鄰村的學校知道的也不收,只好把他送遠點,那裡沒有人知道。」大官的妻子只剩下憂愁。「將來他長大了,娶媳婦都難。現在,誰家得這個病都不敢往外說,怕丟人。」 是的,只要人還沒有死光,丟人的事總是存在的。 就在大官家院牆外的那個幼稚園,已經有五位孩子被趕回家了。從北京讀書回來,想為家鄉的教育做點事的園長底華內疚地說:我也沒有辦法,其他的家長有意見,我留他們,這個幼稚園就辦不下去。我也同情他們,他們的父母到我跟前來哭:我們已經得病,都要死了,就指望孩子能讀點書,將來能自己混口飯吃。可是,底華說,我也沒有辦法。 大官的時日已經不多,他已經有了晚期的症狀,在他死之前,這個世界對他已經關閉了。在燈光下,在他能去的屋子裡,大官安靜地坐在床邊,一個人偷偷翻讀高耀潔編寫的那本《愛滋病/性病的防治》,也許,他想從那裡找到這個世界,這個世界的聲音和這個世界所能給予他的最後關心和安慰。 回去的路上又經過開封古城,這個古城,一千年前曾經是那麼的輝煌壯麗,它的人口有上百萬,它是那時世界上最偉大的城市之一。而今,昔日的景象依稀可辨,「龍亭」四周的燈火像璀璨的花朵,灑在秋夜平靜的湖面上。也許你會說那是美麗,而我只看到那被洪流摧毀的城池,那些被黃河的泥沙掩埋了的屍骨,他們的哭喊呼叫無聲無息。 半個月後,我給東關村的大官打去電話。他的精神彷彿比我見他的時候好,他在電話裡感謝我給他帶的書和藥。我告訴他我不知道我還能做什麼,有什麼能幫上的,儘管說。一直很平靜的大官突然在電話裡哭了,他說:「兄弟,你看我還能活嗎?這病還能治好嗎?」正在他身旁的姐姐搶過電話說:「兄弟,你有文化,幫我們打聽打聽,有什麼藥能治啊?我們家兄弟姐妹幾個哪怕能活一個也好,要不這一家可咋辦啊?我要是能有那麼一天,我一定去給你磕頭。」 大官也許已經看過了我給他帶的那本書,他最後對我說的話平靜而且暗淡:「你看,我們都這樣了,還有人會管我們嗎?將來我們的孩子還能有出路嗎?」 孤兒建龍 九歲的建龍不久前剛剛被改了名字,他現在叫「建設」。原因是村裡的人都認為他名字中的「龍」字是條毒龍,將他的父母都剋死了。「建龍」的父親死於去年年底,母親在今年的五月初也死了。當小建龍的母親被埋葬之後,他就成為村裡眾多的孤兒之一。他現在獨自一人跟著爺爺和奶奶過。 「當初想來想去沒有辦法,我們去打聽哪兒有孤兒院,想送他去,那裡好歹有口飯吃,他死活也不肯去,看他哭得可憐,我們也不忍心……」奶奶一說話就用多皺的手捂住了雙眼。 建龍正當壯年的父母並不是被他剋死的。這一點,所有的村裡人都明白。在村裡,還有許許多多名字裡沒有「龍」的孩子也成為或者即將成為像建龍一樣的孤兒。從去年開始,他們的父母都陸續死於對他們來說並不熟悉的「愛滋病」。 這個離開封市不到四十公里的村莊就是段雁書六一年從部隊轉業時,為了回應「建設共產主義新農村」的號召而回到的屈樓村。在那裡,有點文化的段雁書一直都認為他有責任帶領村民走出困境。當年他轉業的時候,原本可以留在城市裡,做一名幹部,吃國家糧。後來,他發現農村苦,就自己要求回來了。他一遍又一遍地說:「毛主席不是教導過我們,到最困難的地方去?」 當年「最困難的地方」如今也還是。在這個主要靠種植小麥和玉米的村莊裡,人均只有一畝二分地。段雁書坐在他既是廳堂又是睡房同時也是糧倉的平屋裡說:地少,土質也不好,如果種小麥,畝產只有五百斤,每斤賣五毛錢,收成就是兩百五十元,玉米的畝產是六百斤,每斤也是五毛,有三百多塊,這一畝地一年下來也就收個五百多塊錢;每人每年除了交兩百四十斤的公糧外,還得交其他費用,像今年,村裡集資修路,每人又交了一百七十元,這樣下來,每人每年也就得個兩百多塊錢。 貧窮使村民低下了頭,貧窮使一向保守的人們也紛紛地伸出胳膊,不論男人女人,從九一年開始到九六年,「村裡除了老人和小孩,年輕人百分之九十五都去賣血,」段雁書淡淡地說著,「不賣血,連買種子、買化肥、買水澆地的錢都沒有。」 二兒子剛剛死去七天的段雁書,還剩下兩個兒子和兩個女兒。然而,他說除了大女兒在縣裡上班,沒有賣過血,其他的孩子那幾年也都跟著去賣血。而這些活著的兒女們都跟剛剛死去的老二一樣,各有兩個孩子。 二媳婦剛剛到墳地裡哭了一場,被婆婆拖了回來。段雁書勸她說:「你就想寬一點,看看孩子吧,還有孩子呢。」三十四歲的魏紅沒有回答公公的話,她默默地走到煤爐邊去生火,給剛剛放學回來的兒子星星做午飯。她心裡也明白,當年她也跟著丈夫一起,到開封、到鄭州去賣血。她說:「大家都去賣,電視、報紙上都說『獻血』光榮,對身體也好,還能致富,哪知道就得上這個病。」 坐在床上,什麼話也不說,兩眼盯著一台十二吋黑白電視的星星也許並不知道,有一天,他和她十三歲的姐姐也將成為孤兒。 段鴻鈞是段雁書的侄兒,三歲時就沒有了父親,現年六十八歲的母親靠撿拾煤渣把他和另外兩個兄弟拉拔大。現在,在牆角邊的一張破木板床上,他已經躺了三個多月了。他說:這個病咋這麼厲害呢?我原來一百三十多斤的,現在才剩九十斤了(一斤為五百公克)。說完了,他就把頭偏到牆角,彷彿再也無力說話,再也無力看一眼在床邊牙牙學語的兩歲半的兒子段原。 瘦小的奶奶從廚房走了過來,她抱起段原,用手擦了擦小孫子臉上的黑漬。年輕時獨自一人含辛茹苦撫養三個孩子的老母親並不知道她手裡的小孫子和他九歲的姐姐段白在不久的將來也要靠她來撫養,村裡人至今都不敢告訴她,段原的母親也感染了HIV;沒有愛滋病常識的村民也不知道,剛剛出生兩年多的段原其實也有感染的可能。這位已經兒孫滿堂的老母親將帶著她眾多的孫子、孫女步入她的古稀之年。因為她的另外兩個兒子和兒媳婦都曾經賣過血,他們都各有兩個未成年的孩子。 屈樓村是一個有著八百多人口的村莊,像河南其他許許多多的村莊一樣,愛滋病的病毒正活躍在青壯年的身體裡。隨著時間的流逝,他們將在老人和孩子面前一一死去。在那裡,死亡對於他們來說已經成為家常事了,還活著的人在村裡談論身邊的死亡,就像談論已經過去了的饑荒、水患一樣。而滿村的孩子都張著一雙無辜的大眼睛,迷茫望著大人,彷彿在聽一個遙遠的故事。 生命和死亡似乎還有另外一種詮釋,在貧瘠無望的村莊裡,或許人們也不得不接受這另一種詮釋,另一種命運。在這片廣闊如荒漠的土地上,生命的唯一追求不過是能夠將姓氏延續下去。只要不「斷子絕孫」,哪怕卑賤如牲口,哪怕一日三餐嚥下去的除了粗糧,剩下的只是悲哀的淚水。 有一種絕望。是不是有一種絕望,無聲,然而強大,像愛滋病病毒一樣,只在血液裡流傳? 還能讓村裡人惦念著而又一遍遍詢問的是:我們死了,將來,國家管不管我們的孩子?而我的回答卻總是:不知道。小建龍是死去的爸爸和媽媽留給老兩口的唯一紀念,是他們從昏花的雙眼裡還能望到的一點微弱之光,那也許就是全部的未來,如果生活本身還沒有成為一種負擔的話。 死去的父母留下的還有院子裡只剩斷壁殘簷的豬圈,當年,他們也曾滿懷希望,後來,養豬賠了錢,他們就跟人到新疆去摘棉花,再後來,他們在鄭州和開封一帶賣血。「兩口子好歹掙了點錢,託人送回來一千元,後來不能賣了,也不回家,在城裡做生意,說是把養豬欠的貸款還清了再回來。」老奶奶的話語總是被淚水沖涮著。「去年,聽村裡的人說兒子病了,我就到鄭州去接他回來,回來不到兩個月就死了,他一死,媳婦也開始病了……。」 在用賣血得來的錢蓋的磚瓦房裡,七十歲的奶奶佟乃素和七十二歲的爺爺翁長流已經沒有了勞動能力。祖孫三人的生活靠建龍還活著的兩個叔叔和一個伯伯。「平時沒有吃的,就上他們那兒拿點,每個月他們每人還給十塊錢的生活費。」奶奶說:「他們也不容易,孩子的老師來催學費,我們也不敢跟他們張口,老兩口到處去借也借不到,親戚朋友都借光了,他爸爸病的時候,能借的都借過了,到他媽媽死的時候,家裡連埋她的錢都沒有,要是還能賣血,我也去賣了……。」 年輕的夫婦在村頭的墳地裡,再也看不到這日夜流淌著的淚水了。他們也不知道為了能讓年僅九歲的建龍繼續上學,老母親讓老伴到學校去磕頭,讓一百六十元的學費減免了四十塊錢。 老奶奶一遍又一遍地擦乾她的眼淚,最後,她兩眼空空地對著屋子說:要不打著精神往前過,咋辦?我倆一傷心死了,這孩子咋辦? 迷霧中的文樓村 在河南愛滋病的疫情被成功地掩蓋了六年之後,今年八月四日,中央愛滋病防治工作組趕赴河南上蔡縣蘆崗鄉的文樓村。此次由衛生部、民政部組成的工作組,在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的率領下,會同河南省副省長李志斌等地方黨政領導一同入村,開展慰問及醫療救治工作。 這一遲來的行動不管怎麼說確定了愛滋病在河南農村存在的事實,同時,也把這一正在中原大地蔓延的災難濃縮到了文樓這個在過去的一年裡不斷被海內外媒體披露的小小的村莊裡。文樓村因此被更多的人知道了,無論它感染愛滋病病毒的人數是官方所公佈的二四一人,還是村民們所說的「至少四百人」。 一年以前,在我去文樓村的時候,高耀潔囑咐我:去看看吳籠,看看她的病情怎麼樣了,給她的孩子威威帶點吃的。這孩子可憐,才兩歲半,也感染了愛滋病毒。到了村裡,路邊的村民告訴我,吳籠已經在頭一晚死了,在她家的院子裡,小威威被奶奶抱在手上,身上還穿著白色的孝服,那些剛剛送葬回來的男人們一個個沉默地蹲在牆角邊或者屋簷下。 沉默的村民對於外界的來訪也保持沉默,或許是因為還未從悲傷中解脫出來,但依我看,更多是因為擔憂。有些欲言又止的村民總是抬起頭來,怯生生地望著一位三十多歲的年輕人,在他嚴肅的表情下,村民們始終不敢提一句村裡愛滋病的情況。 那位表情嚴肅的年輕人姓孔。據到過文樓村多次的高耀潔介紹,他是村裡讀過書的一位熱血青年,曾經不斷給她寫信,彙報村裡的疫情。在他的一封信裡也談到了他對於這個即將被愛滋病摧毀的村子的擔憂;他甚至提到,等他攢夠了錢,他要上北京,到國務院信訪辦投訴。 這樣的一個青年,在我們提及愛滋病的時候,卻矢口否認,說「那是謠傳」。身邊另外一位憤怒的中年人指天咒罵前一陣報導了文樓愛滋病情況的記者,說他是「喪心病狂」,為了掙稿費,把整個村子的名聲都搞髒了。他說:「現在,村裡的人到外面賣菜都沒人要。」 後來,高耀潔對我說:孔也是沒辦法,他是村幹部,鄉裡、縣裡給他壓力,不讓他往外說。再說,他這樣做本意也是為了村裡好,他怕這事傳出去了,村裡的人無法生活,因為人們都認為這是見不得人的病。 不管怎樣說,採訪是無法進行了。我們踩著泥濘的小路離開了吳籠的家,走到一個胡同口,一位村民突然從牆角裡走出來,小聲地說:我知道誰病了,我帶你們去他家。我們趕緊快步地跟著他走,然而,走不多遠,他就被姓孔的叫住了。我們繼續往回走,這時候,對面小賣部裡跑出來一個人向我招手,大聲地對我說:你來,我託你給高耀潔帶封信。我過去了,原來那個小賣部連著一個小診所,那人是村裡的醫生。他快速地在一張紙上寫著什麼,後來他聽到門口的人跟姓孔的打招呼,就慌張地將那張紙塞進了我的口袋裡。那張紙上寫的是:今年以來,八百人不到的村裡已經有二十多人死於愛滋病了,村裡的孤兒面臨失學,發病的感染者沒錢買藥,地方政府不管我們死活,也不讓我們接觸記者……。 文樓村僅僅是河南上蔡縣的一個普通村莊,它之所以最早被外界知道,是因為武漢的桂希恩教授數次到村裡義務為村民檢測,並向外界公佈了檢測結果:第一次從村裡提取了十一個人的血樣,有十例檢驗出呈陽性,第二次提取了一百四十個人的血樣,有八十多例呈陽性。再後來,他第三次去的時候,他所提取的血樣被當地政府部門沒收,結果也就不為外界所知。 文樓村所處的河南是一個擁有九千萬人口的農業大省(不包括無法登入戶籍的超額生育小孩),農業人口占總人口百分之八十,這超過七千萬的農業人口當中有多少人去賣過血,沒有人可以真正給出一個精確的資料。 五年來一直為幫助愛滋病人而來往於各個村莊的高耀潔認為,溯自九○年代初期,河南開始大興「血漿經濟」,全省各地加起來,至少成立了兩百三十個官辦血站。而河南省一百多個縣分中,有五十多個縣存在著嚴重的賣血問題。她估計:全省賣血人口(包括九八年「獻血法」實施前和實施後)達到一百萬。據省防疫站的兩位專家透露:一九九六年,迫於專家的壓力,河南省衛生廳抽調了「自己」的力量,對全省十三個縣進行了賣血人員愛滋病重點普查,下去普查的人員共普查了約十萬「獻」血員。一位參加沈丘縣調查的人員說:愛滋病毒呈陽性反應的比率,沈丘是百分之八十四,尉氏、西平、上蔡和太康也都很嚴重,最低的一個縣也達到百分之六十七……。 一年多來,在中原的這片土地上,我已經先後到過開封、商丘和駐馬店一帶的一些村莊。在任何一個村莊裡,愛滋病人和他們的家人都生活在一種無知無望而又無助的黑夜裡。病人沒有錢看病,也沒有愛滋病的知識,而去村裡送藥送書的人一旦遇到政府部門的工作人員,又往往被扣押。 村裡賣過血而還未發病的人不願去接受檢查,理由無非檢查太貴,要一百多塊錢,還得加上到城裡的路費;而像桂希恩教授這樣到村裡義務檢查的醫務人員則一再被趕出去,他在文樓村的最後結局是:被打,被罰跪。 我曾經在一個正在死人的村莊裡打電話給上蔡縣防疫站,詢問防疫站掌握的愛滋病情況,接電話的人厲聲地說:「什麼愛滋病?這裡沒有愛滋病!誰批准你來的?通過衛生部門了嗎?」 所有的村莊(除了今年八月以後的文樓村),沒聽說有政府官員去過問一下愛滋病人的情況,也沒有醫療人員前去幫助,哪怕只是告訴他們:你們活不了了,不要再去相信那些號稱能根治愛滋病的江湖郎中了。 汽車總是在高低不平的鄉村公路上行駛,田野中有時長著綠色的莊稼,寬闊的馬路上總有一些農用車,無聲地往前開著,車上總是站滿了禽鳥一樣的農民,而他們也總是從望不到盡頭的馬路上來,消失於望不到盡頭的馬路彼方。 高耀潔曾經不止一次說過,河南的愛滋病情況,如果再不引起政府和社會的重視,那將有可能成為國難,死去的人將比二次大戰死的中國人還要多。中科院院士曾毅也一再警告:中國能用於截制愛滋病的時間和機遇已經不多,若不迅速採取有效措施,中國將成為世界上愛滋病感染人數最多的國家之一。 小小的文樓村,在被政府官員、被媒體「轟炸」過一陣之後,又歸於它死一般的寂靜和絕望。政府新開設的愛滋病診所也僅僅像一塊高大的牌匾,上面彷彿寫著「文樓愛滋病村」,將即將死去的人們擋在裡面,也將關心或者是恐懼它的人擋在了外面。在一封文樓村程姓村民寫來的信中說:「……現在,從外面來的醫務人員一到我村就被『工作組』趕走……在中央衛生部來人時,每個病人發五十元錢,麵粉一袋,毛巾被一條,還有治療口腔黴菌的弗康唑,衛生部的人和跟來的大批記者一走,就什麼都沒有了……。」 曾經轟動一時的村莊又漸漸地被遺忘了,那裡的災難也不再被人們談起。正如我的一位老師所說:這二十年來,有多少內地的城市已經被沿海的大城市遺忘了?有多少鄉村已經被城市遺忘了?又有多少只有貧窮和疾病的鄉村被富裕的鄉村給遺忘了? 發病者不斷死亡,往往一兩個月之後,再回來,就見不到心裡一直惦念著的病人。記得高耀潔跟我說過:「有一位病人,一直給我寫信,讓我有空去看看他,給他帶點藥,我就等,等一拿了工資就去,到了村頭,我打聽這個人,村民問:你找他幹嘛?我說我從鄭州來,來看看他。他們說,老人家,你在這等一會兒就能看到他了。過沒多久,就看到一群婦女唱著喪歌將他的棺木從胡同裡送了出來。」 「中國已經沒有時間再等了。」聯合國兒童基金會駐北京的代表說,中國的愛滋病已經走上了它的「高速軌道」,政府部門所公佈的六十萬帶原者僅僅只是這個軌道上的起點。聯合國發言人在去年的世界愛滋日上就呼籲:除非立即採取行動,否則到二○一○年,中國感染愛滋病的人數將至少達到一千萬。 無論在河南的哪一個角落,一路上,我想得最多的還是那個「文樓村」。那個一出生就感染了愛滋病的小威威是否還活著?那位在我當時無法採訪而正要離開村子的時候,呼天搶地撲到車前哭訴她死去的兒子和兒媳婦的白髮老婦現在怎麼樣了?她帶著的兩個孫子是否已經失學?這些也許只有村裡的人才知道,然而,這個村子是再也進不去了。電話裡也找不到那個姓程的了,高耀潔告訴我他正到處躲,上頭怪他跟記者「亂講話」,要抓他。就在前一陣子,他還每天打電話給我,像孩子似地對我說要到上海治病,而我一直沒有答應。如今,只要看到四周那無邊無際的田野,我內心裡就是一陣內疚。 其實每次打電話過去,我既害怕聽到他已經死去的消息,又擔心接電話的人是他。他死了,但一群人的痛苦和災難不會因為他一個人的消失而消失;假如他還活著,又能怎樣呢?面對這個渴望活下去的脆弱身軀和心靈,我這個健康的人能對他說什麼?能給予他什麼? 應該有人出來承擔責任,為這個驚人的醜聞付出應有的代價!為死去和即將死去的幾十萬、上百萬的生命懺悔!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記得發生在法國的「輸血感染案」,當時,由於HIV剛剛被發現,法國的輸血法案中還未實施對供血者的HIV檢測,結果導致兩千多人感染。這兩千多人的生命讓當時法國的衛生部長辭了職,其他相關失職人員坐牢。 過去的幾個月裡,在一些幾近犯罪的不實報告中宣稱:河南通過非法賣血而感染了愛滋病的人數為三到五萬。這資料我不知道是怎麼來的,我只知道我所走過的任何一個村子(除了文樓),死去的病人和正在發病的人都不被外人所知,他們就像田野裡長的莊稼,死了還是活了,只有本村的村民知道,只有掌握他們命運的季節知道。 文化程度不高的程在信中提出疑問:非法血站的出現是在九五和九六年,為什麼村裡從來沒有在非法血站賣血的人也感染了呢?為什麼已經八歲的兒童也感染了呢?而賣了五年血的東關村的大官卻從來沒有聽說過非法血站。我想提出的疑問是:在中國,哪些人才有能力、才敢去辦非法血站?高耀潔曾經一針見血地說:在河南,愛滋病不是什麼其他的問題,是腐敗的問題。 在中原的大地上,始終折磨我的問題則是:當年,那些血站的血都流到哪兒去了?而用他們的血漿製作出來的血製品又都賣到哪兒去了?前一段的報紙還報導,河北的靳雙英因為在醫院裡輸血而感染了愛滋病,她當時剛出生的女兒佳佳也感染了,她的丈夫王為軍正在為死去的她和他們即將被病毒折磨的四歲女兒狀告沙河市康泰醫院。 在高耀潔這幾年所收到的通過賣血或輸血而感染了愛滋病的四千多封病人來信中,她說:也有安徽的、河北的、山西的、湖北的,中國三十一個省市都有……。 文樓村在我的印象裡總是雲煙繚繞,也許是我離開那裡的時候正值傍晚時分,而下了一整天的雨剛剛停止。那天,當我回到鄭州的時候已經午夜了,跨出車門一抬頭,發現深藍的天空中掛著一輪圓圓的月亮,我的心突然一陣顫抖。我在想,文樓村村頭的那棵高高的楊樹上,是否也有這麼一輪圓月,正安詳地照著這個寂靜的村莊。 後記:高耀潔是鄭州的一個退休婦科醫生,由於她一個人對河南當地政府的鬥爭,使得這一疫情被外界知道,以及她五年來對愛滋病人的幫助,二○○一年八月她獲頒美國「Jonathan Mann」健康與人權獎,雖然她沒能去領獎,但這個組織把獎金寄給她,她用那些獎金出版了她的書《愛滋病/性病的防治》十二萬冊免費贈閱。 【2001-12-04 聯合報】 | 

 本城市首頁
本城市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