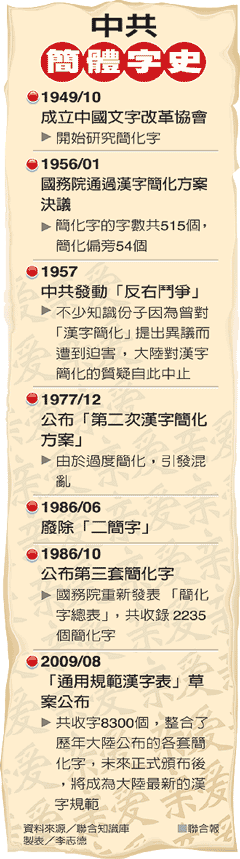游於藝
當代書法,以抒發獨到創見為主,從內容到形式,或辭必己出,或借古喻今,無不以展現時代之精神與一己之妙悟為要旨……
壹
中國書法,源自中國語文。近年來,中國書法通過當代書法家與藝術家之手,以各種變化多端的形式,在國際藝壇大放異彩,引人注目,惹人深思。
關於中國語文,最早在《周禮·地官》中有「六書」之說。到了西漢,劉歆於《七略》才進一步詳解為:「古者八歲入小學,故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謂象形、象事、象意、象聲、轉注、假借,造字之本也。」指出文字符號與自然形象之間,有千絲萬縷、不可分割的關係,為後來「書畫同源」的美學理論,奠定了基礎。
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序〉中分析道:「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此論把書畫同源的看法,進一步推向文字聲音「四聲、五聲」與視覺顏色「五色相生、墨分五色」的對照呼應之上。
之後,唐朝的徐堅在《初學記·卷二十一》中,為中國文字的發展整理出比較完整簡易的說法:「《易》曰『上古結繩以治,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點出中國語文的表現形式,是一種由立體到平面的過程,於是中國語文的形式精義,盡在其中。
「六書」中前三項,與語文之「視覺藝術形式」有關,而語文的內容意義,與其書寫形式,則有辯證性的「結構」與「解構」關係,此乃中國美學之核心,於食、衣、住、行、詩、畫、文章,無所不通。
《韓非子·五蠹》云:「昔者倉頡之作書也,自環者謂之私,背私謂之公。」自環就是結構,可以造出一「私」字,背環自然就解構了,可以造出一「公」字。此乃中文造字的重要原則之一,也是中國書法的美學要義,千古不廢。
這也就是說,中國語文書法可以,歷史與非歷史並行,並時(synchronic)與貫時(diachronic)並進,實用與藝術並存,結構與解構並立,有意義與無意義並構,敘事與抒情聯璧,有形象與無形象同體,對稱與不對稱並列,平面與立體並現。
難怪傳說中的倉頡,生有「雙瞳四目」,證之他所創造的文字特性,可謂有先見之明。緯書《春秋元命苞》記載倉頡「龍顏侈侈,四目靈光,實有睿德,生而能書。於是窮天地之變,仰觀奎星圓曲之勢,俯察龜文鳥羽山川,指掌而創文字」。
因此,中國書法,在語構學上,其形式「基因」,也就是自然界各式各樣平面或立體「點、線、面」的排列組合。在語意學上,中國書法是各個時代個人心聲的反映。在語用學上,中國書法,可與各式各樣的時代精神與姊妹藝術,雜交混種。在書寫工具上,則可指掌、筆墨、非筆墨,共存並榮。在書寫形式上,可以立體、平面交錯共存。在書寫內容上,可以古、今、中、外同時並列。
中國語文中的任何一個字,譬如「樂」字,在藝術書寫形式上,可以平面也可以立體,可以結構式的,以輕快的筆法反映樂的內容,讓內容與形式,合而為一;但也可以解構式的,以痛苦的筆調,或任何不相干的筆法,來書寫樂字。只要書寫結果,能夠通過形式與內容辯證關係,呈現自給自足、隨機應變的多層次生命力,就是書法藝術品的完成。
由是觀之,中國書法可以貫時性的反映中國文字從結繩紀事、龜骨契刻符號、陶文、甲骨文到篆、隸、草、楷的發展,讓形式與內容,大我生活與小我生命,與時代精神,不斷對話俱進。
當然,中國書法也可以並時性的完全抽象,由藝術家開發完全自我私密性的記號系統,與各種時代生活對話。
《淮南子·本經》中記載:「昔者倉頡作書,而天雨粟,鬼夜哭。」《春秋元命苞》亦云「天為雨粟,鬼為夜哭,龍乃潛藏」。張彥遠在《歷代名畫記·敘畫之源流》中解釋說:「頡有四目,仰觀天象。因儷烏龜之跡,遂定書字之形。造化不能藏其祕,故天雨粟;靈怪不能遁其形,故鬼夜哭。是時也,書畫同體而未分,象制肇創而猶略。無以傳其意故有書,無以見其形故有畫,天地聖人之意也。」
是的,文字一出,祖宗經驗可以詳細記錄,後人一看就懂,可承可傳,不必自己從頭摸索,能力與生產力大增,有如天降「餡餅」一般。是的,文字一出,各種混世魔王,在歷史記載的照妖鏡下,紛紛現出原形,無法再欺世盜名,只能自哀。是的!是的!文字一出,蒼龍不必再忙於白日飛天,弘法說教,可以靜靜歸潛,藏於深淵,以象徵記號,默示世人,有待古今智者澄懷觀象,文而明之。
努力於當代書法創作的諸君子,當貫時並時同體,具象抽象聯臂,結構解構並行,成為當代澄懷觀象的智。觀象有得,忽然完完全全回到造字之初,驚見闢地開天之景,於是拔地而起,振臂作書,抒一己之胸臆,與時代對話,滿手煙雲夢幻,牢籠古今中外,一洗萬古長長遠遠荒荒渺渺之晴空。
可以愁煞羅青,嚇死倉頡!
貳
當代書法,以抒發獨到創見為主,從內容到形式,或辭必己出,或借古喻今,無不以展現時代之精神與一己之妙悟為要旨。
徒知抄書或只知抄古書者,謂之「抄書家」或「抄死書家」,此等抄書,無代無之,與當代書法無涉。
徒知寫大字者,謂之「大字報書」、「廣告看板書」、「政治標語書」,數位放大,可以立馬取代,或商業、或裝飾、或布景、或自娛,隨處印製,唾手可得。
不過,若書家所書之大字,筆法堅實,結構精當,墨韻生動,布局奇警,辭意翻新,反映時代,亦有可觀之處,不可偏廢。近人時有以大字炫奇者,內容貧乏因襲,形式掙扎畸形,腕弱氣殭腫脹,破綻敗筆處處,是徒知皮毛模仿日本「墨象大字書」,可謂「字大抄書家」,足供好事家弄筆娛樂,圍觀者捧場熱鬧,有識者齒冷絕倒而已。
殊不知,無論當代或古代書法之創作,首重時代精神之探索與開發,與尺寸大小關係不大,尤其值此任意放大縮小之數位時代,作品之尺寸與展出距離,早已不再是問題。
自鴉片戰爭以來,文化中國,從農業過渡進入工業及後工業社會,約有一百五十年之久,反映前期「自強運動」者,有「碑版雄強」一派;反映中後期「國民革命」及「新生活運動」者,有「標準草書」一派。楷、草之間,能夠自言自立創作書家,亦復代有其人。馬宗霍《書林藻鑑》、劉正成《中國書法全集》,皆可參考。
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至今,已逾甲子有餘。六十年間,誰能以書法領導一時之風騷,尚有待「慧眼家」(serendipper),承先啟後,區分珍珠魚目,排比暫定次序也。


 本城市首頁
本城市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