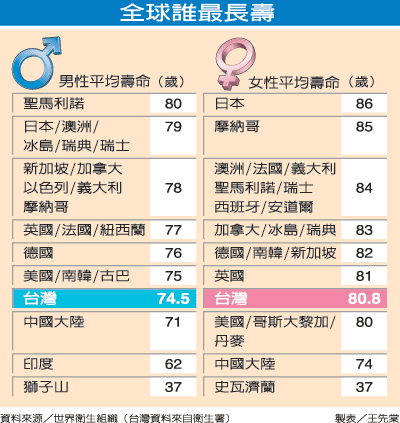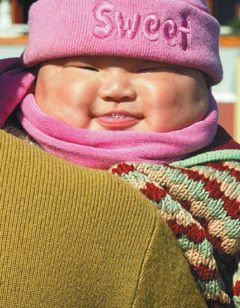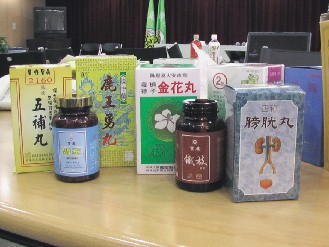初見野原院長時,以為她是寶塚劇團出身的名伶,那也是很多人對她的第一印象。身材高挑臉龐清秀,永遠是一臉春風模樣,實在是看不出她曾經為同時照顧婆婆與媽媽30多年的苦勞模樣,重疊照顧則有15年。她照顧自己的媽媽到87歲、婆婆到104歲的經驗,讓她成為照顧老人的專家,也難怪她被延攬為安養院院長。
野原女士是我在日本當義工的安養院院長,雖然不是時常與她交談,但只要有機會,她很願意和我聊聊老人介護的甘苦談,尤其她知道台灣也逐漸邁向高齡社會,或許很多日本經驗可以分享。
目前在老人介護中,最流行的「從容自在的介護」(不頑張的介護),就是由她提出的,而她所以會有此理念,也是從長期照顧而來的體會。
現年72歲的野原女士說,2、30年前,如果家裡的老人生病倒了,平均介護照顧的期間是半年,身為人子或媳婦,半年的照顧時間在體力上和精神上是可以負荷的。但現代醫藥延命技術進步的結果,一個中風的病人,可以繼續5年、10年或20年的壽命,對照顧者來說,實在不是件輕鬆簡單的工作。
野原女士由自身的經驗知道這是一條長期抗戰的路,得先在心態上有好的心理建設,所以提出「介護,放輕鬆!」的概念,以日文說是「不頑張的介護」,乍看之下好像是不努力照顧,其實不是,這有點像考生進考場考試前,先來個深呼吸的心理建設,之後再好好應戰的感覺。
專業 才能提供優質照護
野原女士以自己照顧的例子說明「忍耐不是美德」,特別是對長期介護而言,長期不休息的抗戰只會帶來身心俱疲的沮喪甚至崩潰,不見得是好事。
她說,為了長期抗戰,「多利用公共的輔助設施」是必要的,「光有對長輩的愛是不夠的,專業才可以照顧得更好」,運用一些提供喘息照顧或日照中心的照顧,將長輩送由專業機構介護的時間,讓介護者可以喘一口氣。
野原女士說,她會利用這段「喘息」時間,好好的看一個展覽,或和好朋友聚聚餐,「介護者更需要被照顧」的想法也由此而來,當介護者也得到很好的安慰或鼓勵後,會有有心力持續照顧長輩。或者利用長輩在午睡的2個小時,到附近小店好好喝一杯咖啡。「唯有對自己夠好,才能夠對別人更好」。她說。
野原女士說,照顧小孩有未來性,你會知道小孩再6年小學畢業,再3年中學畢業,再3年高中畢業……這是有盼望的照顧。而介護長輩,如果是短期性的,身心上的問題不大;但如果是長期的慢性病,不知未來在哪裡。尤其在早年的日本,媳婦照顧長者是天經地義,甚至公婆也認為,好媳婦一定要和公婆住在一起。丈夫是獨子的野原女士很了解自己的責無旁貸,但在長達30年的照顧中,她也曾幾度幾乎崩潰,之後才會提出「從容自在的介護」理念,深獲日本人的推崇。
孝養父母 不可承受之重?
雖然台灣不少對長輩的照顧責任都已委由菲傭承擔,在各國宅或公園中,常出現集體「曬老人」的奇觀。但不容否認的,不是每個家庭都請得起菲傭,所以仍存在很多介護的問題,而照顧責任多半還是落在女性身上。
在日本,像利用日照中心或短期介護甚至是改良居家成為無障礙空間的花費,都可以由介護保險給付,自付額只佔一成,所以人們可以好好利用;顯然日本人在喘息照顧中,可以使用的資源相對比較充裕。對已進入高齡化社會的台灣來說,這是很值得參考的制度。
另外,野原女士也提出「有償介護」,當時在日本引起輿論譁然,因為人們很難接受照顧自己的父母還要付費用的觀念。
有償介護 照顧尊長更平衡
日本並沒有引進菲傭制度,除了安養院之外,所有居家照顧都得由家族中子女子媳們輪流進行。野原在娘家的嫂嫂拒絕獨力照顧婆婆之後,改由四女一媳輪流照顧,但在輪流期間,一直有人推拖沒空、沒體力,還有因為照顧母親而沒有收入等理由,不願承擔照顧的責任,母親就被視為是另一種「人球」,在子女間送來送去。於是野原女士建議拿出母親的錢,提出一個大家覺得合理的代價,付費給照顧者,也就是開始有償介護,如此一來,問題也就解決了。
深諳人性心理的野原女士的想法是,付費有其正面的意義,原本視為義務的照顧,因為金錢的介入,變成是了一種責任。既然拿了錢就得負責,得好好的照顧;再加上被照顧的人畢竟是自己的婆婆或是媽媽,更應該有一種無怨無比較的心態,因此投入照顧的心情也轉趨正面;而當輪值的人有事時,也會有人願意替代了,彼此心甘情願,照顧媽媽的品質變好了。
野原女士認為與其讓母親的存款將來變成遺產,不如拿來當介護費用,如此一來,原本兄妹間為了照顧母親弄得頗有嫌隙的感受,也不見了,大家感情反而變好了。所以當母親過世時的守靈夜,家人談論著母親的一切,都覺得非常圓滿,尤其是在母親過世一年忌日那天,全家相邀將當年的介護所得拿出來,一家人一塊兒做一趟溫泉旅行,在懷念中聯繫情感,感覺很棒。
後來,批評這件事最嚴厲的野原女士的三個親姐姐,都覺得野原女士做法其實是顧及了全家族的感情。這件事在經過輿論的討論後,還有不少人寫信給野原女士,說她說出了很多人不敢說的心事,深諳人生的弱點;慢慢地,「有償介護」在日本也普遍得到認同。
將心比心 正向思考更柔軟
在台灣,有不少人在照顧父母時,會由兄弟姐妹或妯娌間出錢合力由專人照顧,或者委由任一子女照顧,而其中若有子女為了照顧父母將工作辭掉,當然需要金錢繼續日常生活,這部分難道不應該由其他子女予以補貼嗎?也許不少人以為,照顧父母談到錢好像是不孝的舉動,但隱諱不說,可能會讓照顧者有怨難伸,結果無法盡心盡力照顧父母,父母得不到好的生活品質,那不是兩蒙其害嗎?所以野原女士如此為人所不敢言的理念,終究會得到認同。
另外,野原女士著書分享長期介護的心得,像《正正當當的自在照顧》及《介護的魔法語言》,在日本都是暢銷書。
在《介護的魔法語言》一書中,她以自己的心得,利用語言的轉換,也改變了介護的心情。像「以理解代替說服」,就是懂得站在對方立場思考的結果;「以冷靜代替冷淡」,可以讓自己及受照顧者都得到溫暖;「將禍從口出轉成福從口出」,以鼓勵取代責罵;或是「以笑顏戰勝沮喪」等,對照顧者和被照顧者,都很有幫助。
野原女士相信「語言是速效的能量」,以此鼓勵自己從介護中走出來的她,同樣也將心得寫成書,希望為同在介護中過日子的人,能在正向的語言環境中,找到有助生活的陽光。
其實野原女士自己也是與腫瘤共生已達7年的人,堅持不開刀不治療的她說,想以自己可以理解的方法過日子,這也是另一種對自己溫柔的方式。
中國時報 2007.07.12
老人圓夢,到農村!
邱天助


 本城市首頁
本城市首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