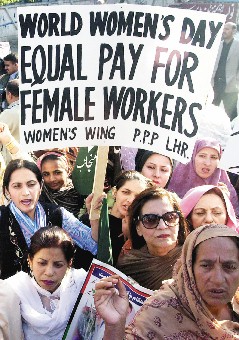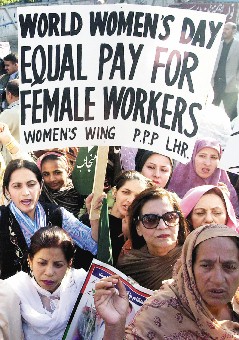| 【文/莫琳‧道(紐約時報專欄作家)、《要男人幹嘛?》作者】 我以為女性主義運動也導致某些正面的結果,包括對女性美的看法更有彈性也更寬容,讓大家從五○年代穿胸甲化濃妝的暴政解放出來。我錯了。女性主義誕生四十年後,女性美的理想典範比以前都還要更嚴苛也更不自然。 就像我的好友克萊格‧畢爾寇說的:「美國有頭有臉有年紀的女人都注滿了牛屁股的脂肪、生化合成的肉毒桿菌和各種火力強大的燃油製品。一大堆林肯夫人都想擁有看起來像拼湊而成的粉嫩年輕偶像外殼。」 我常懷疑,要是女權主義者葛洛麗亞‧史坦能在一九六八年就能未卜先知,看見二○○五年的《億萬未婚夫》(The Bachelor)裡的辣妹打架,還有女人對肉毒桿菌與隆乳的瘋狂,她還會不會大費周章地穿上兔女郎的衣服臥底跑新聞? 史坦能曾經說:「女人讀《花花公子》,感覺有點像猶太人讀納粹手冊。」她有沒有料想到,有一天花花公子兔女郎的T恤會在女性之間引起一陣風靡? 她在一九六六年寫道:「所有女人都是兔女郎。」她並不是在讚美,而是發出女性主義的呼籲要大家起而抗爭。四十年後,這句話已經成為美學的事實,大批女性前仆後繼地臣服於整型刀和注射筒之下,一心想擁有兔女郎的魔鬼曲線。 我們並沒有放寬美麗外表的標準,反而只放寬了我們想追求相同外表的選擇。女人正朝著同一張面孔、同一種身材和同一種表情來發展。 就像艾科夫博士在《紐約時報》上說的:「我們正冒險從事無法想像的行為,」那就是讓美變得乏味。當大家都這麼強調外表,個人認同變得微不足道。好像每個人都寧可選擇戴上面具,也不願意長得像自己,或者像自己的媽媽和姊妹。」 這個世界充滿了突出的植入物和拉平的注射物,誇張的芭比身材就是標準。「好像沒有人注意到兩顆保齡球出現在燙衣板上,是多麼的不協調。」史帝夫‧馬丁在小說《灰姑娘的愛情手套》裡頭如此形容比佛利山的情況。 對美國男人來說,女性美火辣典型的發展是呈一直線,或者應該說是呈曲線──從海報女郎到五○年代的貝蒂‧佩姬(Betty Page),然後是珍‧曼斯菲(Jane Mansfield)到潘蜜拉‧安德森到潔西卡‧辛普森(辛普森的父親本來是青少年傳道者,後來變成女兒的經紀人,他曾經對《GQ》雜誌吹噓自己的女兒穿T恤或者穿胸甲都一樣性感:「她可是有雙D罩杯呢!那兩個玩意兒用什麼也蓋不住啦!」) 女人越來越願意把自己擴張彎曲到誇張的比例,只求能滿足男性的慾望。如今科技就是生物學,所有的女人看起來都像充氣娃娃。她們都選擇芭比有如生化人的豐滿胸脯,以及芭比超低的腰臀比。腰部至少比臀部窄30%,據說這樣最能吸引男人。 厄絲特醫師是身穿香奈兒套裝、腳踩莫諾羅高跟鞋、身材苗條的金髮美女,她會試用所有的皮膚科產品。「在華府,每個人都想成為天生的自然美女。」她說:「我卻要說是後天的自然。大家總是問我:『你有沒有動過什麼手腳?』當然有!不然我們找誰實驗那些雷射?我做過換膚,打過飛梭雷射,做過雷射比基尼除毛。我也用肉毒桿菌和牛膠原蛋白。」 然而,她並不苟同美國對雙峰的造假:「女人隆乳都是為了男人,不是為了自己。而且原因就是幾乎所有整型醫師都是男的。」她說:「我也喜歡尖挺的雙峰,但是我不會去動大手術來達到目的。我會選擇穿上魔術胸罩。」 就像《紐約時報》的記者艾莉克‧庫且斯基(Alex Kuczynski)的觀察:「有那哪男人會把一袋塑膠縫進自己的腿裡?或者把異物放進自己的身體裡?」 但或許女人的變形也是出於她們內心深層的慾望。早期女性主義者竭盡所能地妖魔化芭比,並且貶低女性喜歡瞎拼與化妝的傾向,同時預言一個男人女人都穿著深藍色套裝打領帶在各方面完全平等的世界,實在是太過天真也充滿誤導。 「我覺得追根究柢,女人做這些事不只是為了男人,也是為了自己。」韋絲勒醫師猜測:「我們正在實現小時候玩芭比的幻想。這都和我們的自尊心有關。母親會毫無條件的接納自己的兒子,但是卻總是嫌女兒不夠好。現在我們可以控制自己的長相,就像飲食一樣,那麼何不這麼做呢?厭食症患者有尊嚴嗎?」 但所有人都知道「凡事不能只看表面」,我要抗議,內在美要比外表重要多了。偉大的文學作品和愚蠢的翹臀珍電影都是這樣教我們的啊。我們要怎麼讓女人放鬆,相信這一點呢? 「消滅所有的男人吧。」韋絲勒脫口而出。 (本文轉載自《要男人幹嘛?》,中文譯本將由早安財經文化出版) | 

 本城市首頁
本城市首頁



























 Photo
Phot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