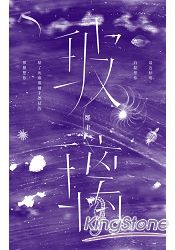
最近好嗎
有點想妳
積了灰塵偶而才擦拭的
那種想你
.
也漸漸明白
每日澆水
總有一天會變成流沙
照顧自己
開始像照顧盆栽一樣困難
常反覆按著
牆上的開關
覺得這輩子全亮或全暗
都只是一瞬間──
都沒關係了。
寂寞是擦拭乾淨
發現中間還隔著一片玻璃
用手指輕輕畫過的
冰涼和曠野
我仍想起了你
不打破什麼的那種
想起了你
鄭聿〈最近的最遠〉
難得假日逛書店,在跳躍的波妞波妞旋律中,發現鄭聿甫出版的《玻璃》詩集,〈最近的最遠〉就在其中。
前陣子感到莫名哀荒,毫無對外聯繫的動力。本想著這倦怠大約只需休養便會自己恢復,但不知為何,同時忽然罹患「閱讀失能」,一本書攤開來,就算是簡淺的散文,眼底所見,於我均是無意義的雜訊,沒有領悟、沒有感動,如同失了故事的小說家,徬徨無依,如此內外交相煎,渾渾噩噩過了幾個月。
然後,某天在副刊讀了鄭聿〈最近的最遠〉。
我完全不是詩人的材料,卻發覺我懂詩的薄霧與沙漠,因詩裡說指出我的病癥。那樣淡泊的寂寞並非頓失安全感而想要陪伴,而是短暫也漫長的人生裡與自己的凝望,與過去舉目相對的心慌。
日復一日,我就這樣陷在斬不斷的心慌裡,人生的用處?生活的侷限?工作的意義?身心的自我價值?……一直想著,想著,想著。有些人追逐夢想,有些人選擇回憶,就這兩件事來說,我似乎是夾在中間進退維谷,艱難的回憶著回憶,卑微的夢想著夢想。
曾經以為自己能不顧一切,後來長大了,漸漸明白無奈、徬徨與妥協才是我生活中的功課。當然,微小的叛逆與堅持仍是有的,但終究得照上天指引的路走,這是我的宿命。玩個文字遊戲。夢想是最近的最遠,而回憶是最遠的最近。
以往的我不停執著的,是最近的最遠:如今讓自己得到安慰的,是最遠的最近。
我將夢想收藏到盒子裡,每天循著生活常軌,同樣時間起床,同一家早餐店不要醬料不要餐具不要塑膠袋,上班途中永遠匆匆一瞥的老米格魯與開落一瞬的蓮花池,夜裡卸下工作壓力後,吃食沐浴打掃與睡眠。數以萬計百無聊賴的日子,僅有回憶能稍稍紓解心靈的乾枯。回憶不一定都美好,但只屬於自己的經歷,全是無可取代的寶藏。
我開始想念童年天真的無畏,想念中學時好奇的衝勁,想念大學時孤獨的熱情……。也想明白,多年以後,我會想念此時氾濫的憂思嗎?鄭聿在〈失眠〉裡寫道,床也有斷崖。何止是床?生活本身就是一座巨大的斷崖。我們每天要小心翼翼確保自己不墜落。或者,有人能在你快跌落時把你拉上來。「好好生活」成為一件時常讓自己感到困窘的事。
鄭聿說他「想成為更少的人」,那樣的心情,我懂。我不喜歡交際、熱情、喧嘩,一如潔淨透明而冰涼的玻璃,什麼都能看見,卻也什麼都不需接觸,對於這世界你了然於心但不需被寫進故事,旁觀而有選擇的自由,自在悲傷期盼落寞都是自己的。
歸零,能夠擁抱廣闊;空白,能夠容納色彩。我努力成為更少的人,而不是封閉的人,邱妙津的封閉是一種絕對的斷裂,也許她不適合我。讀了鄭聿,我開始長出觸角,屏除雜訊,坦然接納俗世的自己。
這樣很好,很好。我要不停對自己正向加強。
本文於 修改第 3 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