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學所學為何?
蔡錦昌
東吳大學社會學系專任副教授
大多數台灣地區學習社會學的學生,不論在學習之前或者學過之後,
都不大清楚社會學究竟學些甚麼。究其原因,實在與社會學這門學問
的特性有關。社會學在各方面都很像哲學。除了社會學本質上就是一
種歷史哲學之演變以外,社會學在現代西方社會科學學術體制中的知
識形象,非常類似哲學在整體知識體制裡的處境— — 雖然聲稱為知識
典範之母,包羅一切,但是一來既無專屬的具體研究範圍和專業知識
的排他性,二來其內部亦學派林立,莫衷一是,令學者無所適從。其
實這兩門學問都是以特殊觀點作為其學科成立之理由。學習社會學,
就是學習其特殊的觀點。
社會學觀點的關鍵在於從「社會條件」(social conditions) 的觀點看一
切,不管事物原來自設的意義體系為何,或者是否還有其他複雜的內
涵。而所謂「社會條件」,其含意大致有四:其一是在特定歷史時空
中被形構成的人群生活模式或人際相與模式,也就是一般所稱的「文
化」或「社會結構」;其二是有助於形構特殊人群生活方式的各種媒
介和佈局,包括觀念、活動、人口、科技、地理等因素;其三是群聚
互動生活所難免的,將事物依優先性和急迫性排序及分類之需求;最
後是人際相與之時行動者為求身心平衡所必須運用的心理機轉與應對
策略。
社會學的「社會」概念跟一般人所想的不同。它屬於一般人日常生活
中無意識的層面,必須翻過一般人想法的後面才掌握得住。故此,學
過社會學的人難免會跟一般人貌合神離。
關鍵詞:社會概念、社會條件、社會學、歷史哲學
在台灣,有七所綜合大學裡面設有社會學系所,有的兼設碩士班,甚至博士班,有的則僅設大學部或只設研究所。[1] 另外有三四所大學設有諸如醫學社會學、教育社會學、資訊社會學等相關學系或研究所。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特別一點的系所,如農業推廣學系、社會心理學系,城鄉研究所、勞工研究所、中山學術研究所裡的社會學組,以及各種與社會工作或社會福利有關的學系或分組,加上師範大學及師範學院裡所設的社會教育學系和社會科教育學系,這些系所的教學內容裡,社會學相關課程也佔著相當的比重。有這麼多大學生和研究生主修或者副修社會學,他們在修習之前或修習之後,究竟知不知道社會學所學的是甚麼呢?令人覺得有點遺憾的是,依我所見所聞判斷,他們似乎並不清楚。[2]
為甚麼會如此呢?究其原因,除了因為這些學生都是以中文來寫作和思考的非西方文化地區學生,對於以歐美現代生活為典範的社會學概念其背後所預設的諸種想法並不熟稔以外,[3] 主要還在於社會學這門學問本身的特性之不容易為人了解上。
社會學是一種歷史哲學
社會學在各方面都很像哲學,而其中特別有關聯的是:社會學本質上就是一種新形態的現代哲學——「歷史哲學」之演變發展,只因為在討論主題方面更專注於所謂「社會生活」的層面,所以才獨立為一門學科而已。[4]
現代哲學的特色,就是造出一個所謂「經驗現象的世界」來,作為人類生存活動的終極場域。正如韋伯所言,現代人所生活的世界乃是個「除魅了的」(disenchanted)世界,[5] 一切發生在這個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受既定內在法則控制的事物,也就是可以用理性了解分析的、具有邏輯關聯性的事物。不過,在這樣一個一切皆「被決定了」的、幾近於「僵死」狀態的世界上,卻上演著各種各式看起來活靈活現而紛紜複雜的事物變化。此種「似活實死」的變化情節,就是「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s)研究的旨趣所在。「經驗科學」研究的旨趣是重建「經驗現象」(empirical phenomena) 背後或之內的結構性法則,並憑之解釋該現象的意義。何謂「經驗現象」呢?所謂「經驗現象」,就是可被人類意識所察知的現象。何謂「現象」?所謂「現象」,就是那些呈現在人類覺知能力之可及範圍內的事象,這些事象皆以「形式」(form)與「內容」(content) 二分結合的方式,或以「觀念」(idea)與「感覺」(sensation) 二分結合的方式存在,因此,一方面可關聯到普同性和恆存性的層面(雖然終究言之仍然屬於一個幾近僵死的有限世界,並非真正的恆存性),另一方面也關聯到個殊性和暫存性的層面。總而言之,現代哲學讓我們生活在一個封閉的、有限定的、可分析的世界中;它提供了「經驗科學」所需的一切,甚至讓「經驗科學」擺出驕傲自滿的姿態,改以「知識」(science) 為名而與仍然糾纏於中世紀神學問題的「哲學」分庭抗禮,獨立自主。
不錯!以「知識獨立」號召的「經驗科學」確是具備獨立自主的充分條件,只不過它不該也不能跟哲學一刀兩斷,否認其本身亦是一種哲學之本質。雖則思想史的世界其實也是個江湖世界,一樣成王敗寇,有力者即有理,以致連康德也以牛頓物理學為典範來重建哲學大廈,從此哲學變成像科學一樣的專業學科,而其專門工作就是為科學作奠基性的思考,而且以此作為哲學的主要存在理由;但是科學本身其實是一種哲學,跟它所極力想保持距離的哲學一樣,都在嘗試構築一些關於終極真理的藍圖,而且也跟哲學一樣,對於自己的結論沒有十足的把握。假如不是思想史中的遊戲規則在作祟的話,科學是不應該隱瞞它跟哲學之間的同源關係的。照理來說,科學應該自稱為一種現代形態的哲學才對!現在可好了!科學將其所以能成立之基礎問題交給哲學來「推想」或「猜想」,而宣稱自己只從事有根有據的經驗性事實研究。這等於意謂「經驗科學」自身的基礎本來就沒有問題,哲學的探討其實是多餘的庸人自擾。這樣的論調簡直是掩耳盜鈴,自欺欺人!
從這樣的視角來看經驗科學,便很容易了解為何它會分出「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或稱「歷史社會科學」)兩大類來,而且後者從來就是以「歷史哲學」的方式存在。因為作為對經驗現象的研究,經驗科學自然就會偏向認同「此地此刻」(here and now)現象之優位性以及偏向信賴可測量控制的研究程序,導致有所謂親身經歷的「一手資料」優於間接知悉的「二手資料」之分別,亦導致數理的統計數據和物理實驗證據較諸文字論述分析更具說服力的看法。因此,在近代西方學術史上,也只有到了像李克特(Heinrich Rickert)和韋伯等這樣出色而有自己獨特見解的新康德主義者出來,才有人敢主張,在經驗科學的天地裡,人文科學優位於自然科學而且文字論述較諸實驗數據更具說服力。[6] 可惜此種意見不中人聽,說了以後也沒多少人注意,至目前為止,大多數的人文社會科學研究,仍然以自然科學為典範。面對自然科學家時,人文社會研究的學者,仍然多少有點兒自慚形穢。[7]
人文社會科學為何從來就是以「歷史哲學」的方式存在呢?因為所謂「歷史哲學」,就是以哲學的方式來看待歷史,亦即從一種整體性的邏輯觀點來理解每一個歷史事件,將每個歷史事件視為可作理論分析的對象,皆有其起因及後果,一如每個自然現象之有其原因與結果一樣;換句話說,「歷史哲學」的旨趣,就是把歷史的論述理論化(theorizing history)。歷史論述一旦理論化,便非常近似人文社會科學,所欠缺的只是發展更多分化和專門化的類型概念,使歷史事件轉化為「社會現象」,不再明顯地緊黏著歷史整體的解釋架構,而能把注意力挪移至個別的歷史情境特性上,讓局部歷史時空中的事物充分顯露其變異性。簡而言之,就是把顯明硬繃的「歷史演變規律」化為暗含柔轉的「社會情境制約」,化整為零,讓解釋空間有更大的迂迴餘地。作為人文社會科學之代表的社會學,就是如此衍生出來的,所以始終保有歷史哲學的特色。
社會學的知識形象
社會學在人文社會科學裡的知識地位,也很像哲學在整體知識界裡的處境。現代哲學號稱為「知識之母」,是知識中的知識,專門研究各門知識之所以成立的理由及其可能的途徑。然而除了「知識論」、「倫理學」和「美學」這三種分別以探討「真」、「善」、「美」為其個別重點的領域以外,哲學並沒有屬於一般人所了解的「專業領域」;而且「知識」、「倫理」、「美感」這三個領域又難以在紛雜的現象世界裡劃出可辨認的界限來,不算是一般人所了解的「領域」。一般人所能分辨的領域,都是一眼看過去即能分辨的具體事物,就像桌子和椅子那樣在那邊,桌子與椅子的不同,大多數人都能一看便知,明白分曉。哲學研究的是一切事物的基本原理。這「一切事物」,包羅太廣,那「基本原理」,又層次太高,都是必須再翻進一兩層才能領會到的抽象層次,一般未受過專門訓練或者對於此種高層次事物不感興趣的人,不大可能想得到或注意到此種事物的存在,遑論分辨其中憑空虛劃的界限了。從反面來說,哲學所處理的題材其實是世界上最普通、最常在的東西,每個人當下便能體證這些事物的存在及其重要性,問題只在所出諸的態度是否嚴肅認真而已。假如態度不夠嚴肅認真,則甚麼樣的生活態度和對事物的看法皆可稱為「哲學」,反正「哲學」的原意就是「愛好智慧」。[8] 如此一來,哲學變得太濫了,領域的劃分也就不重要了。一門學問的專業性,通常會表現在其對非專業者的排他傾向上。如果這門學問的課題誰都有資格發言的話,試問又如何能建立其專業形象呢?學生們花時間費精神來學習,結果又所得為何呢?家長們和各級政府機構又有何理由繼續支持這門學問的教學研究活動呢?
此外,哲學這門學問內部分歧之嚴重,也是導致其給人「空泛游移、難以掌握」之感覺的主因。由於哲學是包羅一切而又高度抽象的學問,對於像「智慧是甚麼?」和「甚麼是值得做的事?」之類的根本問題,可以有多種不同的解答方向,而且它們之間又經常沒有交集,道不同不相為謀;因為說到底,這乃是一個人各有志,性情相異的問題,這裡沒有誰對誰錯,甚至也難論定誰高誰低,只是各適其適,各有千秋罷了。因此,大多數寫「哲學概論」的人,都以羅列古今各種被歸類的哲學派別及其重要主張,來代替解答「何謂哲學?」的問題,甚且有人還理直氣壯地歪說「哲學就是哲學史」。可見情況之嚴重!
作為一個學院中的知識體制單位,哲學系應付上述情況的辦法有二:其一是以重要哲學家的著述和學說作為認別「哲學」所學內容的標誌,見到這些人名和書名,等於見到哲學本身;其二是強調諸如「邏輯學」和「思想方法論」等課程,聲稱這是哲學訓練最重要的功能,也是最顯著的特色。因此,在每個大學的哲學系課程綱要裡,我們都可看到諸如柏拉圖、亞里士多德、笛卡爾、萊布尼茲、康德、黑格爾、尼采、胡塞爾、維根斯坦等名字,也看到諸如《柏拉圖對話錄》、《沉思錄》、《純粹理性批判》、《精神現象學》、《善與惡之外》等書名。當這些被歸類為「哲學」的偉大思想家及其經典名著出現時,誰還能懷疑哲學系的存在理由?誰還會懷疑學哲學的價值?即使大多數人都不清楚這些哲學家說的是甚麼,甚至連哲學系的畢業生也講不明白學過哲學以後身心狀態有何特殊變化,但至少像台灣俗諺所言,「沒吃過豬肉也看過豬走路」,況且他們還特別修習過邏輯思考課程,照理應該比沒學過哲學的人更能理性思考。[9]
社會學在人文社會科學裡的知識地位之所以很像哲學在整體知識領域中的位置,主要原因當然就在社會學本身的歷史哲學背景上。社會學自始至今仍然保有歷史哲學對整體人文知識對象的基本關注,始終以「社會現象」作為其研究對象範圍,繼續在基礎領域上耕耘開墾,保持其作為純粹經驗科學的特性, 不似「經濟學」[10]、「政治學」和「法律學」那樣夾雜著對傳統制度性知識的尊崇以及汲汲於在現實領域中加以應用。[11]
社會學雖然不像哲學那樣曾經是一切世俗知識之母體,從之衍生出諸種知識部門來,但社會學至少是所有社會科學學門的知識典範之母,社會學的研究進路即是社會科學的研究進路。不過這不但並未為社會學帶來學習上的優勢與方便,反而招致不少誤解和疑惑。社會學的研究範圍既包羅一切人文社會現象,以致於無法跟其他社會科學學門劃清界限,以突顯其專門研究領域之特性,同時亦難以藉排斥外行人發言之機會來反顯自身之專業性,建立本門學問之知識權威。一般人聽到「社會學」一詞,都會以為它研究的是所有社會上發生的事情,是一門人人都可參與的、很容易入門而且有趣的學問,因為所有人都活在社會之中,都有各自不同的社會生活經驗,因此都有資格討論關於社會的問題,甚至有人認為自己在社會中打滾多年,閱歷豐富,體驗深刻,比諸在大學校園中讀書出身的社會學家更了解社會生活的真相與真義。類似的誤解也發生在大學之內,只不過想法稍為不同。大學中的人知道,凡是能在大學中成為一門科系的,皆不可能沒有特殊的學術旨趣與研究領域,只是不曉得「社會學」跟「政治學」和「經濟學」有何不相重疊之處而已。假如「社會學」跟「政治學」和「經濟學」並列在「社會科學」的範疇之下的話,「社會學」大概就是專門研究全部社會生活裡「政治」和「經濟」之外的殘餘部分罷。這部分是甚麼呢?有些人想應該是社會上比較次要、比較軟性的諸種制度,包括宗教、教育、家庭、休閒育樂等;有些人則認為應該是社會上各種正式制度之非正式層面,近於一般所謂「文化」的領域。這兩種大學中人對「社會」一詞的意象,並非全無道理,只不過皆不切中核心而已。[12] 「社會」的界限究竟該劃在那裡呢?這實在不是個容易解說得明白的問題!
同樣的,社會學雖然由於歷史很短,從事研究者不如長久以來從事哲學思考者之多,因此其內部之派系,沒有哲學那麼多。然而揆諸社會學研究領域的特性,假以時日,其內部派系應該不會比哲學來得少。為甚麼呢?因為社會學的核心概念——「社會」,同樣既是個全包性的概念,幾乎網羅所有發生在人與人之間的事情,同時也是個必須翻進裡層才能掌握住的概念,並非一眼就可確定的明白之物。因此,不同的研究者可以有不同的「社會」概念,也可側重探討有關社會生活的不同層面,只要言之成理,多少可以跟人群生活掛鉤,都可以說是一種「社會學」。[13] 最妙的是,像「結構主義」(structuralism) 這種學術潮流,專門從廣義的「語言」或「語法」的觀點入手來討論一切文化事物,而且專從所謂「符號」(sign)的作用來分析文化事物的內在邏輯,看起來似乎不像是社會學的研究,但就在其根本設定——社會的就是符號的,因為符號的就是交換的——的立論上,不止也屬於「社會學」的一員,而且幾乎成為「人文科學」(sciences humaines) 的代名詞,其潛力不可限量。另外,像「身體社會學」這樣的新課題,從身體的使用方式上來論證社會約制力的意涵以及社會生活的基礎,也是一種「社會學」,而且很可能會是未來社會學的主流之一。至於像「社會生物學」這樣的流派,主張應該把生物因素(基因決定論)帶回到對社會生活的探討上,不但把「人文」和「自然」重新連接成一體,視前者為後者之延伸,而且將「社會」概念之適用範圍由專屬於人類擴展至人類之外的動物群,這也算是一種「社會學」,雖然它的靈感主要是從基因生物學和動物行為研究那邊得來的。另外,像法國年鑑學派(Annales School)史學所引伸出來的社會史研究,如艾里亞斯(Pilippe Aries)和杜比(Georges Duby)等所帶動的對家飾衣裝、起居飲食等個人生活方式歷史演變的研究,也是一種「社會學」,其社會學分析的含義較諸其表面可見的史料引證更加重要。近二十年來,女性主義甚囂塵上,社會學界亦興起一種以女性主義觀點來論述的「社會學」。在法國,以所謂「後現代」(postmodern)風格的文筆專門評論美國式生活方式的布希亞(Jean Baurilliard),甚至明白標榜「反社會學」或「祛社會學」的立場,認為所謂「社會」已經變成擬象的真實或「過度真實」(hyperreality)了,不再具有基礎性和客觀性。雖然如此,我們卻不能不承認他也是個道地的「社會學家」。
既然社會學內部學說林立,莫衷一是,而學科歷史又不如哲學之長久,因此,作為一個大學中的知識體制單位,社會學系比較不會把「社會學」當成「社會學史」來教,以歷數過去百多年來社會學說的發展來代替回答「社會學是甚麼?」的問題。不過,在應付學科認同的需要方面,社會學系的做法其實跟哲學系的做法差不多,兩者同樣以舉列一些重要學者的名字及其學說作為可認別的內容,只不過在學科訓練特色方面,哲學系強調的是邏輯思考,而社會學系則強調調查統計。[14] 現今一般大學社會學系裡所引以為典範的社會學大師有:馬克思、涂爾幹、韋伯、舒茲(Alfred Schutz)、帕深思(Talcott Parsons)、墨頓 (Robert Merton)、郭夫曼(Erving Goffman)、柏格(Peter Berger)、哈伯瑪斯、魯曼(Niklas Luhmann)、吉登斯 (Anthony Giddens)、 布爾迪厄(Pierre Bourdieu) 等。社會學系也有幾本堪稱為經典的名著,其中最常被提及的有:《社會學方法之規則》、《宗教生活之基本形式》、《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實相之社會建構》、《溝通行動理論》等。[15] 由於這些社會學大師及其作品不如哲學系所認同之哲學家和哲學經典那麼廣為一般受教育者所知悉並推崇,因而也無法產生一如在哲學系裡所產生之正字標誌的招牌作用。幸好社會學系的訓練至少還有強調調查統計的部分。雖然無論就學前後,學生皆不大確定他們所學的內容是甚麼,但總可以憑著所學到的一點調查統計技術謀個生計。
社會學之所以跟哲學相似,遭遇到這些困難,其實都肇因於它們兩者皆是某種知識典範之母,都以特殊觀點作為其學科成立之最終理由,屬於奠基性的學科。學習它們,就是學習它們的觀點。由於觀點並非具體的或者內容性的事物,不容易從字面意思便看得明白,故此假如學者學習時不往此方向探索領會的話,即使花了數年時也不一定能掌握住它們的主旨,甚至說不出它們所學為何。因此,對於那些習慣於一分耕耘必有一分收穫,只想熟記一些具體實用之知識的人而言,這兩門學問都不容易學得好。
社會學的觀點
社會學既然是一門奠基性的學科,此即意謂其觀點一定非常徹底而具有根本性,其涵意不可能是一般日常用語所能道盡的,因為它所開展出來的事物定必在我們日常意識框架之外,而且以「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方式作為我們日常意識框架的後設基礎。社會學觀點的關鍵概念——「社會的」(social)——就是這樣的概念。「社會的」的想法並不像大多數社會學系師生口上說的那麼簡單明了。之所以會覺得簡單明了,只不過因為他們似乎頗有自信地說,說得那麼自然當然,而別人也就唯有順著似懂非懂地聽而已。
社會學的觀點是甚麼呢?簡要言之,社會學的觀點就是從「社會的制約」或「社會的條件」(social conditions) 的觀點來看一切事物,不管該事物原來自設的意為何,也不管其是否另有其他更複雜的內涵。譬如說,「宗教社會學」便是從「社會條件」的角度來討論跟「宗教」有關的諸種現象,上至「何謂宗教?」和「神是否存在?」的問題,下至「宗教組識的科層化」和「神職人員之間的種族歧視」問題等,都在此觀點下討論,不管「宗教」本身是甚麼樣的一種身心狀態,是否一種可被觀察分析的對象,也不管各宗教團體聲稱其宗教經驗之特性為何,甚至不管是否在某些族群生活方式中,有沒有「宗教生活」,或者所謂「宗教生活」在該族群的日常生活中重不重要。換句話說,在宗教社會學的觀點下,「宗教」只是一種「社會現象」,或者說,被化約成只是一種「社會現象」,近似於意底牢結(ideology)。因此,虔誠信教的人不會以宗教社會學的觀點去觀察分析他所信奉的宗教;而作此種分析的人,要不是自己不信奉任何宗教,不然就是他所觀察分析的是別人的宗教教派,或者為了與廣大的世俗科學勢力虛應故事,而專就一些次要的層面作觀察分析。對「宗教」如此,對其他如「藝術」、「哲學」等高深微妙的人類身心經驗也是如此。舉例來說,布爾迪厄對法國教育文化生活的分析便是專從「低層次」或「下限」的角度來討論問題。他專談藝術品味高低之區辨作用所涵蘊的階級認同策略,又談法國的精英大學如何利用教育評等制度製造其精英教育形象。此外,不管男女之間的情感關係內情如何複雜多變,社會學的觀點總是往性別分化、人口結構和時代風尚的方向著手。又譬如我們對日常飲食的感受複雜多端,常有難以言語形容者,然而社會學的觀點只對飲食的規範和風尚及其人口分布的變化方面感到興趣,其他則鮮予理睬。總之,社會學觀點專從所謂「社會的」視角看事物,所以常令那些從事微妙深奧活動的「高級人士」感到不滿;另外,對待內情複雜的事物也顯得以偏概全,罔顧實情,徒讓人覺得有隔靴搔癢,中看不中用的遺憾。
在說明何謂「社會的」的想法之前,還必須先交代一下「制約條件」是甚麼。所謂「制約」或「條件」,[16] 所指的是一種受約束的關係,亦即某事物或某事物的特質之所以能存在,所必須依照或仰賴的因素;只不過「制約」一詞側重其「依照」或「仰賴」的關係特性,而「條件」一詞則側重其「因素」的內容特性,所以,最好的全譯名是「制約性的條件」。制約性的條件可以有好多種形態。不過,在社會學的天地裡,通常遇到的約有三種,分別是:韋伯的「適當的因果作用」(adequate causality)、馬克思和涂爾幹式的「結構的決定」(structural determination) [17]和一般社會調查研究的「統計因果關係」(statistical causal relation)。[18]在此三種制約條件當中,就明確性以及可控制性而言,以韋伯的想法制約性最弱,馬涂式的想法次之,而制約性最強的是因果關係。不過,這並非意謂韋伯的制約想法比較不重要,或者比較稀鬆不實;相反的,這反而是更重要,更精確更客觀的想法。只因為我們受了太多牛頓物理學的機械式世界觀的影響,篤信 x® y 的因果關係想法,才會這樣想。[19]
韋伯之所以主張社會科學只求掌握「適當的因果作用」,而不求得到全盤完整的因果說明,原因在於一來他不認為我們能夠重新經歷一次所要研究的事情,二來他也認為不必要這樣做,因為不管在科學天地裡或者在日常生活中,從來就不曾有人對全盤的因果脈絡感到興趣,大家想求得的都是某特定事件的主要因果脈絡而已。全知等於無知。因此,我們所能知而且所應知的是:根據我們的知識興趣以及參考一些有效的經驗法則而經由抽象化思維過程所綜合出來的因果關係脈絡,其主旨在於確立事情發生的「客觀可能性」。韋伯在他著名的《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一書中特別示範了一種他稱作「選擇的親和關係」(elective affinity) 的適當因果作用。他說:他所建構的「基督新教倫理」概念,跟同樣是他所建構的「資本主義精神」概念,兩者之間有著「選擇性的親和關係」,亦即兩者因同具「合理性」(rationality) 之生活風格(life style)而可能經由行動者有意或無意之間相互援引並彼此增強,近似於中國話所謂「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或者「臭味相投」。[20] 由於只是「相應」、「相投」,所以「由其中一方制約另一方」的意味,便變得頗不確定。馬克思和涂爾幹的「結構決定」,就比較有「其中一方制約另一方」的意味了。在馬涂兩人而言,發揮制約力的一方就是事物之結構面,包括「社會生活方式」和「媒介特性」這一而二,二而一的兩種因素在內。譬如馬克思談到資本主義社會時,便明白以「資本」或其具體代表「金錢」作為此一歷史階段社會生活的主要媒介,而透過此媒介所開展出來的生活方式即是「市場經濟」的生活方式。因此,資本和市場經濟,就是此時期的「下層建築」(Unterbau)。它偏袒一切跟它相配合而受它指導的事物,而排除或忽略那些不順應就範的事物。它不明白主動強壓那些不配合它特質的事物,只是形成了一個環境和局勢,逼得那些事物不得不順應就範,不然就沒有繼續存在的機會。涂爾幹的「結構決定」想法也差不多,只是比較具有「基本形式」(elementary form) 的意味,即一般所謂「文化」或「世界觀」的意味。[21] 至於一般社會調查研究的「因果關係」想法,盡量把一切制約因素化為各個獨立的變項,進而求其可數量化的相關性,這在在都是 x® y 基本想法的延伸,力求掌握一個能產生可預期效果之確定的 x導因,以遂其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ationality)[22] 之控制欲望。雖然這 x® y 不一定都在實際的「時間1 ® 時間 2」之設定框架中進行,但是這種簡單的時空序列性的框架意象總是形影不離。這種制約想法雖然不無意義,然而如果不加省思地為量化而量化,以為改善了統計的工具性手段就等於科學進步有了保證,這並不是正宗科學理性的想法(只能算是流行的想法),也不是道地社會學式的想法。正宗的科學理性必定全心全意瞄準盯緊所研究的對象事物,生怕在開始之處差之毫釐,往後便謬以千里。道地的社會學式想法也是時刻扣緊「社會是甚麼?」和「甚麼是社會的?」等焦點問題來論事的,力氣並不全費在如何測量相關度上。把力氣全費在統計分析上,這是識小體而不識大體的表現。涂爾幹是個道地的社會學家。他在著名的《自殺論》中如何運用統計資料來證成他的社會制約觀念,便是一個好典範。涂爾幹的統計功夫可能並不頂好,多有可商榷之處,但是就社會學分析而言,《自殺論》十分成功,有扭轉乾坤之威力。[23]
制約條件並不是一項獨立的思想要素。它跟「社會的」概念其實是相互配合的,有甚麼樣「社會的」的概念,就有甚麼樣的制約想法。以下將就「社會的」的概念再進一步闡明社會學觀點的特色。
何謂「社會的」?
本文開頭說過,社會學本質上是一種哲學。因此,照理社會學也應該跟哲學一樣,在討論時會時刻關照到基本問題。沒錯!社會學的確如此。它的確跟哲學一樣,時刻照應到它的基礎,常去翻修,而且從之得到理智的力量。不過,作為一種現代形態的新哲學,社會學所能透進的基礎只停留在「社會的」經驗層次上,其思考格局亦無法脫離「主體/客體」、「目的/手段」、「應然/實然」、「行動/結構」等二分法的左右;也就是說,在討論到最基本的問題如「事物是甚麼?」、「事物如何存在?」、「如何為真為假?」時,社會學只能從「社會的」經驗層次上立論。職是之故,社會學天地裡的事物都是「社會的」經驗層次中的事物。當然,社會學就主張:除了「社會的」經驗之物以外,別無他物;即有他物,亦非其所能論定。
請問「社會的」經驗層次為何?「社會的」經驗層次,就是經由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所造成的人類身心狀態變化。因此,「社會的」就是「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所造成的身心效果」。社會學主張:一切事物的存在與變化皆因人與人之間的來往而成,連地球的存在與運轉亦然。[24]
究竟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會產生甚麼樣的身心效果呢?這至少有三點可說:第一,人與人之間的來往,猶如鏡子與鏡子之間的反射一樣,會增加身心狀態的強度。我們的信念和勇氣之所以如此堅定,都是因為別人把我們的信念和勇氣反射回我們身上(不管是正面的還是負面的),使力道倍增之故。[25] 第二,人與人之間的來往會提高外表特徵的重要性,助長以貌取人的習慣。所有表情姿勢、語言文物、制度風俗,都是讓人憑以推斷別人身心狀態的外顯特徵。這是人與人之間交往的主要管道。[26] 第三,人與人之間的來往,強迫事物相互比較,也強迫人跟人以不平等的方式相處。一個人沒得比較,或者沒甚麼好比較,但是兩個人在一起,便事事皆可比較。不但從異同比較中得到分類的知識,而且由於人與人相處時人的身心反應特別強烈,外表特徵又成為主要憑據,所以這些分類的知識都是帶有強烈好惡意味,而經常以諸如「對/錯」、「高/低」、「美/醜」、「友/敵」的二分方式來表現的知識。因此,人與人之間不大可能有平等的關係。即使表面平等了,實際上還是不平等。[27] 總之,人際來往會使人身不由己而不自知。
「社會的」的概念其實並不與「個人的」(personal)和「個體的」(in-dividual) 概念背離太遠。[28] 一般人不學社會學,才直覺地以為「社會的」等於「集體的」(collective),既然是「集體的」,就應該跟「個體的」相反,也應該跟「個人的」意思相背離。他們之所以會這樣想,關鍵即在思考不夠徹底,沒有扣緊根本問題。他們眼中的人,只是一個個關在軀體單位裡的行為者,而所謂「社會」,則是這些一個個的人的集合,或者存在於這些一個個的人之間的東西。他們沒想過,「個人」和「個體」是怎麼產生的。「個人」和「個體」都是隨著「社會」一起出現的想法。無論就觀念史而言,或者就形成原理而言,皆然。[29] 「社會」的概念並不偏袒集體而忽略個體,幾乎相反,個體意識愈強時,「社會」意識也愈顯著。理由很簡單:因為「社會」非但不是可見可觸的具體事物,而且也不是註定和固定存在於某處的抽象事物,而是在人與人進行相互交往時身心狀態變化的產物,是間接經由人的意識變化所撐持起來的,或者倒過來說,它是人的意識變化所必須間接徵引到的抽象事物。無論就被研究者來說,或者就研究者來說,皆是如此。[30] 學過社會學的人用「社會」一詞,跟沒學過社會學的人用「社會」一詞,意思不一樣。前者是當下直接就事物之一般分類印象而認定的,而後者則是疏離於一般分類印象而再翻過一層,才間接認定的。[31] 一般人認為,像人口、家庭、交易量、國家、教科書、國際組識等就是「社會的」事物,認為研究它們就是研究社會現象。不知道光是它們本身,不足以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而只是些空泛而籠統的抽象概念。要使它們成為社會學的研究對象,必須先經過一翻對具體情況的綜合研判,以確定在某特定歷史時空情境之中,這些概念是如何在一個關係網絡中起作用而確立其意義的。確定了它們在可能之關係網絡中的位置及其作用以後,它們才成為社會學研究的對象。從社會學的觀點來說,它們才是「社會的」現象。[32] 舉例來說,光是「人口」本身,不成為一個社會現象。除非我們從某個歷史時空情境的階級結構入手或者從性別關係入手去看它,它才成為有意義的社會現象。「物價」亦然。如果談論它時沒有同時想到,有一定的人口在某種被決定的狀況下從事生產,另外有某種家庭或者社群須要購買那些物品,政府又為了政權的安定而盡力調度控制;如果這樣,它也不成為一個社會現象。反過來說,如果像台北縣觀音山這麼一座山,只要我們從台灣民間習俗的觀點來談論它,它便成為一個社會事物,而不是個自然事物。
涂爾幹的社會學雖然有點極端,被批評為「社會學主義」(sociologism)[33],但是他的「社會」概念的確能振聾發瞶,摒除俗見。涂爾幹說,「社會」就是「道德」(morality)[34] ,而「道德」乃是人性的養成所及發用地。最原始但也是最深入人心的「道德」形態是「宗教」,所以「宗教」生活就是原始的「社會」生活,也是人類首出之「文化」生活方式。人類因為有「宗教」生活,所以才首度有機會成為人類,所以人不能不過「社會」生活,因為「社會」生活始終帶有其原初的「宗教」含義,而道理不變。涂爾幹之所以說:「神即是社會。拜神即是拜社會。」[35] 緣故在此。此外,涂爾幹的「社會」亦非一個完整地存在於那邊的事物,像撞球桌上的白球那樣,能撞過來影響我們的位置和移動方向(也就是 x→y 的方式)。涂爾幹說,「社會」是個擠出來的、冒出來的特性。它比組成它的個別成員之和還要多出一點東西來。[36] 原因是「社會」雖由個別成員組成,而且透過個別成員的身心意識來體現和運作,但是「社會」不等於這些個別成員心理狀態的集合,而是他們相處在一起時所產生的身心變化效果——在集體亢奮的狀態下,每個成員都崇奉同樣的象徵體系,而且因此自認為同屬一族。這樣的身心狀態及其憑以發用的象徵體系,特別是其所涵蘊的全體觀及世界觀,方是對個別成員產生制約力的出處。因此可以說,「社會」猶如一齣戲,是由個別成員自編自導自演而成的。沒人演,光有戲碼,便沒戲。有人演,但沒戲碼,也不成戲。涂爾幹強調「社會」在個別成員之「外」,意思是在其未經反省的日常意識之外,相當於「當局者迷」或者「相忘於江湖」之意,非指在個別成員的身心之外的虛空之中有一種稱作「社會」的幽靈存在。涂爾幹力主社會學是一門經驗科學,相當於人文界的物理學,不可能主張如此反科學的荒誕之論。[37]
「社會」與「歷史」都是全包性的人文經驗對象概念,究竟兩者之間有多大的重疊部分呢?兩者之間怎麼分呢?有人可能答說,「社會」側重靜態面和結構面,而「歷史」則側重動態面和變遷面。也可能有人答說,「社會」側重普遍面和律則面,而「歷史」則側重特殊面和個案面。沒錯!這兩個答法基本上跟涂爾幹和韋伯的意見相同。他們也認為:社會學跟歷史學根本是連體嬰,天生就連在一塊分不開,只是各有其側重點而已。[38] 因此,就科學方法而言,只有「歷史社會學」(historical sociology)與「社會史」(social history)之小別;除非所謂「歷史學」所指的是不注重理論思考和類型分析的傳統史學,否則不會有「社會學」與「歷史學」之大分。由此更可見「社會的」概念不可抽離於歷史經驗情境來設想。
何謂「社會條件」?
既然上面已經分別就「制約條件」和「社會的」兩個概念稍作解釋了,接下來便該針對本文最重要的概念——「社會條件」——詳加討論。
能發揮制約作用的社會因素其實很多,只不過在社會學文獻中通常見到的是下述四種:其一是在特定歷史時空中被形構成的人群生活方式或人際相與方式,也就是一般所稱的「文化」或「社會結構」;其二是有助於形構特殊人群生活方式的各種媒介和佈局,包括觀念、活動、人口、科技、地理等因素;其三是群聚互動生活所難免的將事物依優先性和急迫性排序及分類之需求;最後是人際相與之時行動者為求身心平衡所必須運用的心理機轉與應對策略。
第一種社會條件最為常見。古典大師如馬克思、涂爾幹、韋伯等的社會學論述,皆以此種因素為主要訴求。含有濃厚歐陸理論意味之現象學和結構主義傾向的研究亦然。甚至美國社會學的四大主流——結構功能論(structural functionalism)、衝突論(conflict theory)、象徵互動論(symbolic interactionism)和交換論(exchange theory)——也同樣以此為重要的著眼點。「文化」或「社會結構」所指的乃是具體文物體制背後的基礎,此種基礎以「結構」(structure)或「結構化」(structuration)的方式起作用,是人們日常言行的參考架構。[39] 雖然所謂「結構」,人言人殊,語意擺盪的幅度頗大,不過大致說來,要不是指一種具有穩定性的「行為模式」,便是指一種具有穩定性的「思維模式」。「行為模式」所指的是具體行為可認同的模態,亦即在某個社群生活範圍內經常可見的那些行為,所具有之十分近似的樣態(譬如某族結婚過程中送禮的行為模式、現代國家兒童上學受教育的行為模式、二次大戰期間日本軍官效忠天皇的想法等)。至於這些所謂「行為」,有的僅指外表可見的動作,如眨眼、跑步、吐白沫、填黑調查表格中的圓洞等;有的則指包含思慮在內的整套動作,如交換禮物、下棋、建築房屋等;有的指包含思想觀念在內的處事態度,如效忠天皇的想法、捐助環保團體、欣賞夜景等。「思維模式」則專指行為所依循的程序原則,包括行為的規則和行為規則之所以可能的思維法則(譬如台灣的車子靠右行駛,駕駛座在左,而香港的車子靠左行駛,駕駛座在右;又如中國人尚右貶左,但道教儀禮卻常以左手為敬;又如世界各族的宗教和世界觀都有「神聖/凡俗」二元對立的基本分類架構等)。此處所謂「思維」,並非指處在時間變化中的一種心理行為,而是指這種心理行為的邏輯(即意識的結構),是可以脫離具體心思行為內容來討論的層面,其分析結果類似於語言學的語法或者數學的方程式和座標圖。結構主義興起以後,此種想法更為流行。[40]
第二種社會條件較少受到注意,而且出現較晚。因為一般做學問的人都是內涵論者及本質論者,不是媒介論者和效用論者,他們以為媒介和佈局都只是工具、手段或者過程而已,並不是他們所要的事物本身,因此,他們所想所講的,都是事物的結構與意義以及事物形貌的變化,很少能夠想到事物本身乃是身心狀態變化所虛撐出來的結果,事物無本質,其性質依其起作用的方式而定,而且,與其說事物形貌起了變化,倒不如說事物根本已經改變了,消失了。媒介論者之看待事物,好比是銀幕上的電影內容一樣,不過是一幕幕的影象而已。影象是靠操縱顏色與線條的組合方式產生出來的,其形貌很不穩定,而且其效用有部分須依賴觀眾的錯覺來助成。[41] 在古典社會學大師之中,涂爾幹晚年大作《宗教生活之基本形式》,可以說就是一部從活動佈局及其效用的角度來闡明「社會」之起源及其結構特質的作品。在這部作品中,涂爾幹以澳洲土著部落的集體祭典活動為例,詳論土著如何透過此種活動方式,身上便會產生以部族圖騰為注意力焦點的集體亢奮狀態,從而虛拱出三合一的集體意識來:一為神聖的圖騰標誌、二為神聖的圖騰物、三為神聖的圖騰族人。馬克思分析資本主義社會生活之特質時所談到的「資本」和韋伯討論基督新教論理時所談到的「預選說」,同樣具有媒介的含義。其他如艾里亞斯描述童年概念之起源及其特質時所談到的「學校」、殷尼斯(Harold Innis)對大西洋兩岸皮草貿易以及對橫跨加拿大鐵路的分析,還有不少專門闡發諸如印刷媒介對近代西方文化的決定性影響、族群語言對思維方式的左右等,皆屬此類。[42] 大致言之,能發揮「社會」制約作用的媒介事物或活動佈局,皆具有「大宗性」和「牽動性」,亦即該事物或佈局經常大宗地發生而且牽動到大多數人生活中的核心地帶,因而能夠產生強迫因應就範於它的效果。例如一胎化政策之於中國大陸社會生活、選舉活動之於台灣的政治生態,電燈之於人類作息方式、論文寫作之於高等教育及學術研究,乾旱之於衣索匹亞人的族群關係等,即屬此類。[43]
第三種社會條件又比第二種更少受到注意。原因是一般社會學者都是平等主義者,容易把方法論上的平等主義移情為存有論上的平等主義,以滿足其知識分子的軟心腸情懷;因此,他們下意識地拒絕承認,社會上各種不平等現象以及各種不合理制度常具有其所以能存在的理由,有時候甚至還是社會生活之所以可能的積極理由。正如本文前面曾經提到過的,社會學所研究的人群生活方式基本上是近數百年來歐美地區城市裡布爾喬亞的人群生活方式。布爾喬亞以平等的陌生人身分相交接於城市地區,就像今日大學生相聚於城市中的大學裡一樣,傳統身分地位的階層劃分方式無形中大部分皆被拋棄掉了,餘下來的便只有因合作處事時所免不了的,必須依事情的輕重緩急排出優先順序以及依任務大小排出高低階序的需要。在像古希臘城邦那樣小規模的自由民社群裡,這本來不算甚麼,影響不大。然而在大量平等的陌生人頻繁地交往處事的城市裡就不同了。這種所謂「社會的」相處情境具有一種脅迫性(也可以說是暴力性),逼迫人「秀才遇著兵,有理說不清」,平等與合理幾乎不可能。可是很弔詭的,偏偏在這種生活形態下,平等與合理的呼聲卻響徹雲霄,成為公眾的理想,每個人口頭上都贊成此理想,常譴責不合此理想的現狀,要求改革,私底下卻不這樣做,或者不認為這樣做行得通。因此之故,即連社會學家也甚少從此角度來分析社會現象。只有少數專長政治軍事研究的人,才會甘冒不韙,作馬基維利式的主張,明白標舉諸如「無產階級專政」、「科層體制」、「卡理斯瑪」(charisma)、「寡頭鐵律」、獅子與狐狸兩種「精英的輪替」、「總罷工的神話暴力」、「品味的區辨」、「身體政治」等見解。[44] 此種相應於「統治之必然」的社會條件,經常深藏在最黑暗的角落和最惹人反感的體制當中,研究者必須克服自己的小市民心態,提高對權力運作機制的敏感度,才能洞悉個中玄機。
第四種社會條件經常被誤認為屬於個人心理範圍,至多也只跟小團體中的人際關係有關,所以很少人視之為道地的社會制約因素。一般人心目中的「社會」,大概都是「民族國家」(nation-state);小部分人偶爾也會想到像協會、公司、聯合會等社團組織;甚至也有人想到像作家群、上流社會、愛鳥人士等身分群體或興趣群體;但是鮮少有人認為三五個人的社交場合也是「社會」。其實我們的社會生活從來都以三五人的社交場合為主(打從嬰兒時期只在家裡跟父母兄弟相處,直到成年以後在工作單位開會或者洽辦業務,在街上開車,在店裡購物,甚至臨終前在醫院病榻上急救,都是此種場合),即使位居要津,常須面對大群聽眾演說,也只不過是此種場合之延伸變化而已,基本形態未曾有變。[45] 不過,這三五人的社交場合並非僅與這三五人有關而已。他們之間的一言一行莫不與整體大社會有關,甚至可以說,以「民族國家」為主的「社會」,就隱含地實現在這三五人的互動之中;假若這三五人之間互動不良,從小見大,見微知著,可知整體大社會也同樣危危乎,好不到那裡去。在三五人互動的場合中,最重要的是達致身心狀態的平衡,而其關鍵就在於能否成功地在別人心目中造出一種自己認同的自我形象來。做法無他,就是善加控制利用那些間接傳達自我訊息的外顯行為。在人際交往當中,人人都是互相窺視,互相透過對方的外在行為來間接推斷其自我,以便因應對付的。此種有如人間煉獄的處境,迫使每個人不得不順著別人的眼光和說話來做人。當面接觸之時固然須來個渾身解數,互有攻防一番,即便平日獨自一人時,也須模擬準備,預演各種攻守戰略,以免臨陣時措手不及,表現不佳。其中最事半功倍的策略,就是化戰時為平時,採取諸如前台與後台區隔分離的策略,選擇並佈置有利於自己前台表演的情境,而且只讓觀眾出現在此種情境中,同時將不利於表演的後台情境防堵隱藏起來,只讓那些跟自己合夥演出的人參與其中。其他互動策略如:採取偽裝或假惺惺的做法敷衍一時、化後台為前台騙倒對手、看時機如何聯合次要敵人打擊主要敵人、貌合神離以明哲保身、適度地開玩笑以突破對方的壓力網並且顯示自己的實力等等,不一而足。從這個角度入手來分析社會現象的社會學家,都屬於廣義的象徵互動論者,其中著名的有庫里(Charles H. Cooley)、米德(George H. Mead)、齊邁爾(Georg Simmel)、布魯默(Herbert Blumer)、郭夫曼等。[46] 在他們看來,社會生活是個無形的舞台,個人的自我其實是個舞台上的角色,只不過常常假戲真做而已。
從無意識層面入手
社會學既然是一種新形態的歷史哲學,對於人類整體生活有著徹底的看法,那麼就應該在其觀點中處處展露出此種徹底性的特色來。除了論事之時扣緊著「社會的」的基本概念用力,認真落實從「社會條件」的觀點來分析事理以外,還有一種展露此種徹底性的方式,就是專從「無意識」(unconscious) 的層面入手論事。[47]
「無意識」的層面是甚麼?它有甚麼特性?此處所謂「無意識」,並非專指佛洛依德心理分析所謂「無意識」(Unconscious) ,而是泛指一切行動者行動時意識所及範圍之外的層面,這些層面是可以經由專注的反省與分析(也就是專注的意識化活動)而意識化的。無意識層面之所以如此重要,其緣故約有如下幾點:第一,它是對比結構中的深層面和基礎面,就好像視網膜之於視象一樣,沒有了它,意識層面便不可能清楚出現。第二,人的意識狀態通常是區域性的和焦點性的,它所籠罩的領域不及於它自身之外,就像打著手電筒在漆黑的地洞中前進一樣,經常因時易境遷而措手不及,效果逆轉。第三,如果意識內容所產生的身心壓力太大,大部分內容便會或自動或被迫而隱遁在意識之外,只留看起來莫名其妙的一小部分在意識範圍內,就像沉在水底的走私貨品留一個小浮標在水面上一樣。
對事物作無情的、徹底的社會學分析,大概會得出一些甚麼樣的結果來呢?答案是:大概會得出一些跟一般人想法相反,或者離開一般人想法頗遠的看法來。此處姑且舉幾個例子來說明。第一個例子是:譬如當一般住在文明都市裡的人只知道鈔票是用來買東西的貨幣時,我們便舉非洲土著的生活為例,以對顯出此種想法不一定全世界都行得通;或者我們模仿經濟學家的口吻說,假如有一天紙張價格非常昂貴,貴到連印行千元美金大鈔都花不來時,請問還會有鈔票嗎?以突顯此種想法之不周全,只能算是暫時可用的想法而已。第二個例子是:一般人總是不假思索便認為,各種分類法都是從被分類的事物所具有的特性中歸結出來的;但是我們會反過來說,在未有分類架構之前,人們根本不知道有甚麼事物存在,因此,至少那些基本的分類架構是先無中生有出來的。第三個例子是:家長和學校老師常認為有些小孩天性就比較乖,比較聽話,但是我們認為,這些聽話的學生只不過以為自己受到老師的重視,或者曾經被老師和校長摸過頭說:「你是個乖孩子,要給同學做個好榜樣啊!」所以他們在無可無不可的心情下,姑且稍為做得比自己平日的表現好一點,以敷衍一下老師迂愚的好意,如此日復一日,久了以後,習慣成自然了,在「盛情難卻」、「眾怒難犯」之下,也不好說改就改,從此才成為一個乖孩子。第四個例子是:美國南部佛羅里達州的州政府為了保護該州的短吻鱷,免於獵殺滅種之虞,遂頒令禁止獵捕短吻鱷。然而如此一來,便斷絕了那些原本經營沼澤區獵鱷農場的農家的生計了。於是他們紛紛抽乾澤水,填土翻耕,改種作物或者養殖別的禽畜。由於這樣做大量減少了有利於短吻鱷生存繁殖的棲息環境,結果經過一段時間之後,該州短吻鱷的數量反而減少到幾於滅種了。[48]
為了省力與方便,一般人都是依仗意識能力及意識內容來過日常生活的。除非遇到挫折和意外,否則不會費力氣去作反省和分析的功夫。哲學家和科學家則不然。他們的任務就是故意去做這種功夫,故意跟一般人日常生活的身心狀態相反,故意往無意識的層面中去探索。當然,哲學家和科學家在做此種功夫時,並不活在一般人的日常生活中,所以並不講求省力與方便,而是活在一種類似修道人的特殊群體中,以求得「無用之用,是為大用」的智慧。
不過,專注往無意識層面去挖掘,是很傷人感情的事。因為此種做法,基本上就像本文前面提到過的那樣,含有「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的暗算意味,即使本非惡意,但是其結果還是會傷到人的。出家人教訓在家人,在家人甘願聽,因為這是站在出家人立場所說的話,不會勉強在家人去照著做。但是哲學家和科學家說一些批評一般人想法的話,一般人可就不願意聽了,因為哲學家和科學家所過的也是一般人的生活,而且聲稱所研究的就是一般人生活的道理,假如他們的分析和評斷是對的話,那麼一般人的想法就錯了。一般人是真正的世俗之人,哲學家和科學家卻是俗世中的修行者。試問這兩種人怎能不衝突呢?社會學家若想兩全其美,既可以貫徹反省無意識層次的功夫,又不會惹怒一般人,恐怕唯有多利用「見人說人話,見鬼說鬼話」和「貌合神離」的做人策略了。[49]
[1]分別是台灣大學、政治大學、中興大學、東吳大學、輔仁大學、東海大學的社會學系和清華大學的社會學人類學研究所。
[2]譬如說,在某個大學博覽會的招生攤位上,一位社會學系畢業的招生組職員被考生詢問到,究竟社會學系學些甚麼時,連他也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另外,有不少社會學系的畢業生都有以下類似的經驗:他們在謀職應徵時,常被招聘單位主管好奇詢問,究竟社會學學的是甚麼。每當遇到這種情況時,他們通常也沒辦法解說清楚。我相信,假如不是為了寫這篇文章而對這個問題思索過的話,驟然被學生問到時,恐怕連我這個擁有社會學博士學位的社會學老師也會答不上來。
[3]我以前曾為文談論台灣地區社會學理論教學的問題,文中曾就此點加以探討。參見拙著〈談台灣社會學理論教學的一些問題〉,《東吳大學政治社會學報》第8期,民國73年,頁181-192。中文思考之影響到社會學的學習,從「社會」一詞之不易理解上可見一斑。「社會」一詞的意思,並不如台灣學生所想的那樣,意指簡單的「人群聚合成一體」而已。「社會」這個譯詞中所謂的「人」,乃是一種特定身心狀態的人,這種人與其同類之間才須要透過「共同意識」和「法律規範」來往。這種特定身心狀態的人,最早出現在十七世紀西歐城市地區叫「布爾喬亞」( bourgeois,即居住在城市裡的自由民,通常以小商人和基層司法人員為主,而且多數信奉基督新教 )的人身上。布爾喬亞才是本著「個體」的、具有「自我」的身心狀態而與人相處的人群品種。當然,隨著三個多世紀以來的世局發展,此種人群品種已然經歷某些演變,於今已成為最有勢力的品種而遍佈於全球各種城市地區中。凡是接受過中等以上教育而生活在小康水準以上的城市居民,大概都是多少具有類似身心狀態的人。印刷媒介發達與現代西式學校教育乃是造就出此種特殊身心狀態人群品種的主要因素。此現象在非西方文化地區尤其明顯。
[4]此種關於社會學本質的看法,一定有很多人不贊同。讀社會學的人會說:社會學是一門經驗科學(empirical science),以科學的態度與方法研究實質社會生活經驗之內在法則,怎麼可能是一種哲學?讀哲學的人也會說:社會學本身是一門經驗科學,研究的是經驗性的實在(empirical reality),不屬於哲學範疇;只有社會學方法論的高層次部分屬於社會科學哲學,而社會學理論中的一部分屬於社會哲學;因為哲學所研究的是基本原則問題,不是經驗現象的法則問題,而且不採用經驗科學的方法來研究。以上這兩種說法基本上沒有錯,只不過說得不夠深入,而且對學術史仍然持著進步觀的看法,認為學術發展一向都朝著分化和專化的方向走,愈是分化專化,學術就愈進步和完善。(比如說,有一些社會學學者認為,社會思想史所講的基本上是一些未成熟的社會學理論,並非社會學學生一定得熟知的內容,故此建議將社會思想史從必修課程改為選修。)不錯!社會學的確是一門經驗科學,研究的是經驗現象,不像哲學那樣以研究基本原則為主,然而若果稍為深入追究一下,就會發現所謂「經驗科學」也者,其實就是一種「唯物論式的宇宙論」,認為一切事物皆依一定原理發生於由時間和空間所舖成的既存世界之內。此種宇宙論之中有關意識的部分就是一種「歷史哲學」(所以「歷史哲學」就是把意識也當作一種事物的宇宙論,或者把意識世界視為如同物質世界一樣具有其內建運作法則的宇宙論)。社會學就是「歷史哲學」的延伸與變形。孔德、斯賓塞、馬克思的學說不必說了,即連常常批評孔德、斯賓塞之社會學的涂爾幹和一再對黑格爾和馬克思之歷史哲學表示不滿的韋伯,亦只是不滿意他們那種歷史哲學所蘊涵的「整體實在論」而已,並非反對「歷史哲學」的一般設定。「歷史哲學」雖倡導自赫德(J.-G. Herder),但早已由維科(G. Vico)出版於1744年的《新科學》奠定其基礎。維科在《新科學》中明白揭示:人的歷史是人自己造出來的,而人就活在自己所造的歷史之中。此原理真是「歷史哲學」的精髓!因為「歷史哲學」就是百分之百屬於人的哲學。當然,這種人亦百分之百屬於他所造出來的歷史。關於這方面的討論,請參考以下的文獻:Alfred N. Whitehead, Science and the Modern World, Free Press, 1967, ch.1; Leo Strauss, Natural Right and History,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68, ch.2; Carlo Antoni, From History to Sociology: The Transition in German Historical Thinking, Wayne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59, ‘Translator’s Introduction”; Giambattista Vico, The New Science of Giambattista Vico,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84, “Introduction”. 至於何謂「社會生活」的層面,請見本文後半段的論述。
[5]所謂「除魅」,簡而言之,就是把傳統世界中那些神秘古怪的巫法事物祛除掉,使世界上的事物全變成毫無天賦差別意義的事物,一切全由後天人為,而且受一種既定的內在法則統治。換句話說,在除魅了的世界中,一切都變成平均、穩定、清楚、循理,變成可以擺在研究者面前研究分析的「死寂之物」。請參考拙著〈欲力之理法與歷史之弔詭:對韋伯《基督新教倫理與資本主義精神》之詮釋〉一文,收錄在拙著《韋伯社會科學方法論釋義》,台北:唐山,1994,頁125-144。
[6]同上拙著,頁115,附註103。又參見Heinrich Rickert 原著,涂紀亮譯《文化科學與自然科學》,台北:谷風,1987,頁159。
[7]參見Immanuel Wallerstein等原著《開放社會科學:重建社會科學報告書》,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1996,頁5-6。
[8]譬如說「環保哲學」,就是注重環境保護的生活態度;「衣裝哲學」,就是某人對穿衣治裝的見解。
[9]主流的西方哲學跟邏輯思考分不開,這是無可疑議的。但是一來,不同的學派對於「邏輯是甚麼?」有不同的解答;二來,近幾十年來有所謂「先蘇哲學」(即在蘇格拉底之前的哲學)、「存在主義」和「解構主義」(deconstructionism) 等不重邏輯思考,甚至質疑並調侃邏輯思考的思潮出現;所以現在的哲學系已經不那麼注重邏輯學課程了,代之而起的是更注重科學哲學和社會哲學。
[10]此處將「文化人類學」視為「社會學」的姊妹學問,包含在「社會學」之內。至於「文化人類學」的傳統形態——「民族學」(ethnology),則因與傳統形態的歷史學相近,故此不算是經驗的社會科學之一部分。
[11]譬如學經濟學的人通常必須費精神熟悉各種交易制度和稅制的運作,又花功夫作統計分析以便預測未來的經濟情勢;學政治學的人通常必須熟知總統制與內閣制的差別,而且了解現今選舉運作的遊戲規則及政治團體的內情;學法律學的人通常必須熟悉某些法規的制度屬性而且熟背一些法條,兼且花時間學習法庭辯論的技巧。總之,它們都不以純粹社會科學自居,其屬於社會科學的部分都是以社會學為研究進路的部分,如「經濟社會學」、「政治社會學」、「法律社會學」等。
[12]詳情請見下文論述。
[13]文化人類學亦常面對此種處境。因為所謂「人類」及所謂「文化」,亦是此種既包羅一切又莫測高深的概念,既讓一般人覺得籠統糢糊,又讓學者們可各說各話,自成一格。
[14]雖然美國式的主流社會學仍然視調查統計的知識為必要的學科訓練內容,然而由於七○年代以後歐洲社會理論興起,其中多有質疑調查統計等量化研究之價值者,加上另外又翻起了一股跟哲學、文學和文化人類學合流的「文化批評」或「文化分析」,偏向使用質化的研究方法,因此整體而言,量化傾向的調查統計訓練已經不像以前那樣唯我獨尊了,參與觀察法和文本分析法漸有與之分庭抗禮的態勢。
[15]此處所舉述的是現今大學裡社會學系所認同的大師和名著,不包括人類學系所認同者在內。雖然就研究對象及學科屬性而言,文化人類學與社會學實在是一對姐妹花,可是目前兩者在研究進路和知識體制上仍然各據地盤,互有特色,以致兩者在學術認同的內容方面出入頗大,重疊的部分最多只有三分之一。
[16]拉丁文con+dicio。con 是「共同」,dicio 是「說話」,所以原意為「同意」,即同意受所約定的條件做事。
[17]這就是馬克思常說的「決定」(Bestimmung)之意。不過,由於「結構」的另一面就是「媒介」(medium),所以我借用了 Harold Innis 所著的 The Bias of Communication (Toronto: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51) 和Yves de la Haye 所編的Marx & Engels on the Means of Communic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General, 1979) 兩書中的見解,發明了一個用語——「媒介的偏向」(mediational bias)。當然,馬克思和涂爾幹本人沒使用過這樣的術語。
[18]此處姑且以Morris Rosenberg 所談的「變項之間的因果關係」為主。參見 Morris Rosenberg 原著,徐正光、黃順二譯《調查分析的邏輯》,台北:黎明,1979。
[19]韋伯的客觀精神尤其表現在他不強求建立一個由科學理性統治的世界上。他的社會學觀點是最具有自省性和自制力的,也因而繃得最緊。
[20]Max Weber, The Protestant Ethic and the Spirit of Capitalism, trans. by Talcott Parsons, New York: Scribner‘s, 1958, p.91. 由於連美國社會學大師 Talcott Parsons 的英譯本都沒有清楚把「選擇性的親和關係」譯出來,中文本更不必說了,所以我建議參考同註5拙著,頁83-86 的專論,以及頁140註六。關於「適當的因果作用」,同樣請參考此書頁64-69之專論。
[21]涂爾幹的想法與「社會的」概念特別相關,故此在下文會有些交代。此處不擬再細細分辨馬涂兩人結構觀念的差異,只提供一條線索供大家參考,就是先比較一下帕深思結構功能論的結構概念、李維史陀(Claude Levi-Strauss) 結構主義的結構概念以及阿杜塞(Louis Althusser) 結構論馬克思主義的結構概念,三者之間的差別。有了梗概的了解以後,再回頭來細辨馬涂二人之間的差異。理由是馬涂兩人的著作中並沒有使用「結構」一詞,或者把此詞當成重要術語來用,而帕李阿三人則然。
[22]這是法蘭克福學派批判理論所銳意批駁的想法。簡單而言,「工具理性」就是強化「手段® 目的」之間關係中的手段面,甚至最後把手段也當成目的,一切行事皆手段化,以追求更有效的手段作為一切事物的目的。
[23]尤其是把一般視為當然屬於個人心理現象的自殺行為,扭轉為屬於社會現象,這樣的逆反思考簡直神乎其技,別開生面。
[24]只有上過現代學校讀書的人,才知道並確信地球存在這回事。單就此點而言,即足以支持「地球也是個社會概念」的主張。或許有人會疑慮這樣的說法是否恰當,會不會有誇大其詞之嫌。他們認為地球的存在是個被發現的事實,而不是個被創造的信念。但是請問,如果不是自小上學讀書,而現在這些讀過書的人又眾口爍金的話,地球怎麼會存在?不信的話,可以去找一個新幾內亞島的土著問一下,便知道地球是否只存在我們這種人的身上了。或許仍有人不服氣,爭辯說社會生活只是人類整體生活的一個重要部分,並非全部,社會生活之外,還有自然界和超自然界,另外還有個人的內心世界;社會學只是應用科學方法研究這部分的人類生活,不應該反過來以宗教或者意識型態的姿態評斷所有的事情。但是請問,為甚麼對這樣的世界觀如此自信呢?難道不是一群人相濡以沫的結果嗎?社會學如果只是用科學方法研究社會生活的話,那麼請問「文學社會學」和「知識社會學」能成立嗎?如果說連這些看起來十分個人心理性的領域也有社會交往的一面可研究的話,那麼「科學社會學」也可以成立了,「社會學的社會學」也沒問題了。如此下來,豈不是任何人類生活的部分都有社會生活的一面可研究嗎?甚至連相信社會生活只是人類生活整體之一部分這件事,也可就其社會交往面來討論嗎?如果就這一面來討論的話,豈不是可以聲稱連這個信念也是因為自小上學讀書和現今大家眾口爍金的結果嗎?
[25]一個小學生獨自在家裡唸誦ㄅㄆㄇㄈ,效果大大比不上一群小學生在教室裡跟著老師一起唸誦。如果沒有別的情敵競爭,追求者就不會那麼賣力獻殷勤。如果觀眾稀稀落落,便會讓人覺得某個晚會不值得參加。
[26]中國人的紅白兩色分別用在喜事和喪事上,很好辨認。另外有所謂「人要衣裝,佛要金裝」,又說「先敬來衣後敬人」,外表之重要可見一斑。說話沒有牛津腔,即使拿出牛津大學的畢業證書來,別人還以為你偽造文書呢!金錢與數字之所以在商場非常重要,即是因為它們具有最容易為人辨識的外在特徵。
[27]平等主義其實是一種特殊的不平等主張。平等主義強迫人依最普通最表面的特徵來判斷人,而且強迫每個人以同等的份量說話做事。如此一來,在不同階層之間而言,只會對那些習慣使用文字和數字的都市中產階層人士有利,他們比較習慣文書作業以及談判程序,對於權利義務分得比較清楚。在其他人群關係方面而言,大人勢必須將就小孩,陪小孩玩,講小孩話;男人勢必須將就女人,學女人的方式溫柔待人,照顧家庭;老師勢必須將就學生,放任選擇,教一些夢幻性的想法;健康的人勢必須將就殘障的人,費功夫敷設專用設施,又特別花時間配合他們作息。
[28]就性情和存在感受而言是「個人」,就行為和計算單位而言是「個體」。person 原意是演員所戴的臉譜,而 individual 則是不可再分割的單位之意。
[29]就觀念史 (history of idea)而言,「個人」與「個體」的觀念最早出現於公元十一世紀的少數作品中,但真正較為人知的是十六世紀法蘭西的蒙田 (Michel de Montaigne)。到了法國大革命之前,盧梭 (Jean-Jacques Rousseau)對個體自由的推崇以及對兒童人格的歌頌,不知感動了多少西歐地區的文人,令他們嚮往至今仍然威力不減的人權觀念。然而弔詭的是,蒙田和盧梭在提倡個人尊嚴和個體自由之時,也一併摧毀了傳統舊體制而助成了現代的體制——「社會」。「社會」就是以個體主義為骨幹的新型人際相與方式,而個體主義乃是最具有「社會」特性的觀念形態。
[30]這是我綜合馬克思、涂爾幹、韋伯、米德(George Herbert Mead)等古典社會學大師的見解,以及諸如舒茲、郭夫曼、柏格等人的看法,所得出來的結果。此處似乎不夫可能一一引證我的參考文獻,並作詮釋論述。就本文目前的需要而言,應該可以借用如下兩種文獻來暫時支持我的論點。其一是 Peter Berger & Thomas Luckmann, 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Reality, New York: Anchor Books, 1967. 此書專就被研究者的意識變化來討論「社會」之存在。其二是三則選文,分別選自馬克思、韋伯和涂爾幹的方法論著作,收在:Pierre Bourdieu, et al., eds. Le metier de sociologue, Paris: Mouton, 1983, ch.2, “La constuction de l’objet,” pp.193-206. 此三則選文專就「社會」之為研究者研究時所建構之對象來討論。
[31]此處強調要「跟一般人直接的想法決裂」。此點十分重要,幾乎可說是社會學家能否成為科學研究者的關鍵。參考 Bourdieu 等編,同上書,ch.1, “La rupture,” pp.125-192.
[32]Peter Berger有一段話最後表達這種須翻一翻的意思。見氏著 Invitation to Sociology: A Humanistic Perspective, Doubleday, 1963, pp.27-28.(中譯文在黃樹仁、劉雅靈譯《社會學導引》,台北:巨流,民國71年,頁33。)這段話是:‘The social, as an object of inquiry, is not a segregated field of human activity. Rather, (to borrow a phrase from Lutheran sacramental theology) it is present “in, with and under” many different fields of such activity.’
[33]即主張社會學為最優秀的人文學術,不但可以含概並解決所有人類生活的問題,而且還是人類自我了解的至高表現。
[34]請注意!法文所謂 moralite,跟現代中文所謂「道德」,意思有點不同。moralite 指的是人從社會生活中學來的生活習慣及規範,也就是他作為社群一分子所承繼的待人處事心態。這跟現代中文使用者所謂「仁義道德」無關。譬如說,習俗規定女子月事來時不可入廟拜神。這是 moralite,但不是「仁義道德」。
[35]這些見解都出自涂爾幹的晚年大著《宗教生活之基本形式》(The Elementary Forms of Religious Life) 。涂爾幹這句話很惹人反感,因為這句話太像涂爾幹之前的孔德(Auguste Comte)的主張。孔德認為社會學乃是人類知識的最高表現和最後總結,社會學家就是崇尚科學之新時代的教士;因此,在科學發展至巔峰之時,也就是人類的人性表現達至最高狀態之時,人類所拜的神就應該是人類自身。晚年的孔德因而創立了「人道教」(Religion of Humanity)。
[36]這就是他的名言:「全體不等於部分的總和。」
[37]涂爾幹銳意反對「個人心理」與「社會制度」這種簡單物化的兩分法思考,特別強調社會學不是心理學之延伸。他並不否認有「個人心理」這種「自成一類」(sui generis) 的經驗現象層面,只不過他認為此種層面純屬個體,雖與人類整體生活有關聯,但在經驗對象領域之劃分上,跟社會現象全然是兩回事,不可混為一談。涂爾幹不但認為「集體心理學」一詞不合理,而且還反對使用「人際心理學」一詞來突顯社會學的特色。(參見Anthony Giddens, ed. & tr., Emile Durkheim: Selected Writings, London: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2, pp.73-77.)現在雖然已經有很多學過社會學的人會說,「社會學的社會心理學」不同於「心 理學的社會心理學」,但是他們仍然把「社會」跟「心理」擺在同一個平面上,視之為連續體,故此仍然以混淆的方式使用「社會心理學」一詞。這種人或者很勤於研究,心得也很多,但是應該補修社會科學方法論或者社會科學哲學的課程;否則的話,他的研究恐怕會滯留在既膚淺又混淆的狀態而無法進步。
[38]涂韋兩人社會學的趣味雖然不同,前者社會學意味更濃而後者歷史學意味更深,但是對於這個問題的態度卻大致相同。參見同上書,pp.78-79.另外請參考同註5 拙著,頁108關於韋伯看法的論述。
[39]絕大多數的社會學家都認為社會生活就是「體制性」或「體制下」(institutional)的生活。雖然並非全部社會生活內容都體制化,或者每項社會行為都具有體制化的傾向,但至少體制化的行為是社會生活中最受到注意而且是比較具有解釋說服力的一面,所以社會學研究很容易便變成體制性生活的研究。「體制」與「社會」之間的關聯如此緊密,恐怕與「社會」概念之布爾喬亞背景有關。請參考註2的論述。至於「結構」與「結構化」的差別,則相當於靜態的結果與動態的過程之間的差別。像Anthony Giddens就認為「結構化」更加重要,強調在此過程中,當事者(agent)更具有改革能動力。參見氏著The Constitution of Society, Berkeley: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4, ch.1.
[40]結構主義語言學之父,瑞士語言學家索緒爾(Ferdinand de Saussure),1900年左右即提出其著名的二分架構:langue/parole來,認為語言研究應著重在前者(相當於語言的語法層面)而非後者(相當於語言的實際話語層面)。後來結構主義人類學之父,法國人類學家李維史陀所謂synchronic/diachronic之分(即「同時性」與「貫時性」之分)便是此分法架構的延伸。
[41]媒介論的基本觀念是「媒介反客為主,無意識地決定了被媒介的內容。」麥克魯漢(Marshall McLuhan)的成名著作《了解媒介》(Understanding Media: The Extensions of Man, New York: McGraw-Hill, 1964.) 是此方面的代表作。
[42]關於艾里亞斯童年概念的大意及其與印刷書籍興起之間的關係,請參考Neil Postman原著,茆蕭昭君譯《童年的消逝》,台北:遠流,1994,第三章〈童年的起源〉。關於殷尼斯和麥克魯漢媒介研究的概要,請參考DanielJ. Czitrom, Media and the American Mind: From Morse to McLuhan, The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82, ch.6.(中譯文是陳世敏譯《美國大眾傳播思潮:從摩斯到麥克魯漢》,台北:遠流,1994,第六章)
[43]並非凡是大量發生的事物即具有「社會」制約作用。台灣的男性人口和女性人口都各有至少一千萬人,每人每日都至少吃三餐,也都睡眠七小時左右,發生次數不可謂不大量矣,然而這樣的人口活動不算是社會條件,因為它們只是一些週邊性的社會生活基本狀況而已,並非能幫助我們了解與說明特殊研究主題之關鍵因素,一時之間既不牽動大多數人的生活核心,亦不算是可從事或者可不從事的大宗活動。
[44]「無產階級專政」是馬克思的概念。「科層體制」和「卡理斯瑪」是韋伯的概念。至於「寡頭鐵律」,則是德國政治社會理論家米契爾斯(Robert Michels)的概念。「精英的輪替」是義大利古典社會學大師巴烈圖(Vilfredo Pareto)的概念。「繌罷工的神話暴力」是法國社會思想家索黑(Georges Sorel)的見解。「品味的區辨」是布爾迪厄的見解。「身體政治」是英國女人類學家道格拉絲(Mary Douglas)的概念。由於文獻繁多,此處從略不列。
[45]因為演講者演講之時,通常皆視聽眾為一個對手單位。如果聽眾之中有他認識的人或者他特別重視的人在,他通常就會以說給這幾個人聽的方式來演講。
[46]在此我極力推薦郭夫曼那本膾炙人口的成名作The Presentation of Self in Everyday Life (New York: Doubleday Anchor Books, 1959.)
[47]墨頓有名的一對概念:「顯性功能/隱性功能」(manifest function/ latent function),其旨趣即與此有關。墨頓說,大多數有成果的社會學研究都著眼於社會因素的隱性功能,只有少數著眼於其顯性功能。他所謂「顯性/隱性」,就是行動者有意識而為相對於行動者無意識而為之意。參見Robert Merton, Social Theory and Social Structure, New York: Free Press, 1968,pp.73-138. 中譯文請參考黃瑞祺編譯《現代社會學結構功能論選讀》,台北:巨流,民國70年,頁31-100。
[48]此例子引自Anthony Giddens, Social Theory and Modern Sociology, Stand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7, p.9.
[49]Peter Berger稱此種做人策略為「社會學的馬基維利主義」。請參考同註32氏著,ch.7, pp.151-163.(中譯本第七章,頁151-162)
期待「否決模式」向「解決模式」進化
2015-01-20 01:24:40 聯合報 社論
台灣政治具有很強的對立文化,這一方面具有監督作用,可以避免腐化;另一方面卻也導致施政的窒礙難行及反覆不定,計畫動輒擱置延宕。九合一選後的局勢便是如此,不少新任首長不斷推翻前任的建設和施政計畫,以示自己的「新政」作風。我們要提醒的是,如果只有「否決」,而不能提出「解決」,其實沒有進步的意義。
舉例而言,柯文哲連日來針對台北市多項BOT案力槓財團,包括就松山文創園區責備富邦集團「社會觀感不佳」,為大巨蛋建案怒罵遠雄集團「無法無天」,並痛批由鴻海集團承包的台北秋葉原建案「賣得太便宜」云云。有些財團唯利是圖不擇手段,不妨鳴鼓而攻之,也能贏得民眾掌聲。然而,這些案件均涉及公共建設,市府是計畫的主要當事人,掌握有全部的資料;柯文哲應該逐案檢視,就其中問題找出解決之道,或加重罰責,或從市政權責中找出制裁之道,使計畫更臻完美,而不能只是憑著權威任意貶損他人。
柯文哲正值盛氣凌人之際,有些財團不敢直接和他對槓,只能摸摸鼻子,自認倒楣了事。但怒罵一通之後,如果一切都沒改變,終歸是作秀及發洩罷了,於事無補。而碰上郭台銘這種不願忍氣吞聲的企業家,大張旗鼓反擊,要柯文哲四十八小時內還他清白;如此相互叫陣,而其間是非黑白依舊不明,除了徒然擾亂社會人心,又有何用?
柯文哲拆忠孝西路公車專用道、拆除昆陽陸橋、償還若干健保欠款,都顯示他的魄力,贏得市民叫好。然而政策有長期/短期之分,施政有除弊/興利之別,只做短期或只會除弊,其實都不夠;要有長期的興利作為,才能為台北市創造真正的價值。以社子島的開發為例,不論要選擇「曼哈頓模式」或「阿姆斯特丹模式」,都必須提出可靠的評估,而不是憑自己的第一印象率爾全盤否決前人計畫。無論如何,柯文哲必須承認,許多市政議題的專業度和複雜度遠超乎其醫師的知識及經驗範疇,他必須虛心學習。
談到政治上的杯葛,民進黨更是此中翹楚。以《兩岸服貿協議》與《兩岸協議監督條例》為例,由於綠營的抵制,在立法院已經躺了一年多,既不審理,也不表決;難道是要等到民進黨執政,才肯放它過關?再如高鐵的財務改善案,民進黨反對交通部的計畫,自己卻又提不出更佳的解決途徑,只是一味杯葛;俟交通部放棄財改方案打算改走「接管」一途,民進黨卻又去阻擋獎參條例的修法,不許政府接管高鐵。像這樣的反對黨,不必動腦出任何主意,只需坐在那裡搖頭說「不」,擋住對手的每一條路,居然也在選舉中大獲人民的選票獎勵;政治落到如此簡單、弱智的地步,台灣怎麼有進步的希望?
不可否認,台北文創園區或遠雄巨蛋的BOT可能都因當初簽約不夠謹慎,才會留下各種後遺症,讓外界覺得市府「吃了虧」或「圖利財團」。柯文哲如果厲害,應該設法抓住對方要害,設法在權利金或罰款上扳回一城,或者將不平等條約之癥結公諸社會,讓後人不致重蹈覆轍,那才是高明的解決。而不是利用「陰謀論」一竿子打翻一船人,把所有官員都當成貪庸之輩,並抹殺企業經營者在其間付出的努力。
台灣近廿年來的倒退,已到了令人驚心的地步。除了國民所得降低、年輕族群失業率高、教育品質下滑外,更嚴重的是,政府幾乎沒有凝聚共識的能力,長期及大型的建設規劃完全停滯,人民對國家前途感到迷茫失措。最令人失望的是,朝野政治人物每天在那裡叫陣互鬥,從來不是以「解決問題」為目標,而是競以「相互否決」為手段,目的只在彰顯自己的聲威。這種「否決模式」,也許能逞一時之快,也許能抒心頭之怒,卻不可能為社會帶來進步的推力。
台灣如果不想淪為弱智社會,民眾必須鞭策政治人物思考,大家拒絕接受「不」作為答案。選民要追問政治人物:「你有什麼更好方案?」「你的理由是什麼?」這樣才能逼他們把問題想清楚。政治人物只有從「否定模式」向「解決模式」進化,台灣的政治與經濟才有進化的可能。
官場風評:價碼公道
2015-01-16 02:01:39 聯合報 黑白集
高雄市府兩名建管副處長陳國雄、李政賢接連涉貪。令人驚訝的是,陳國雄上月才被移送法辦,李政賢接管業務後繼續收賄,家中紅包放得到處都是,簡直把收錢當例行公事。
諷刺的是,在廠商口中,李政賢的風評不錯;原因是他「價碼公道」,只要業者按行規辦理,大都可以過關。深度解讀,這就是:盜亦有道,官亦有盜,「價碼合理就是好官」,這難道是高雄官場文化的創新標準?建管官員以「價格公道」贏得廠商好評,也算是台灣民主政治「官場現形」的一頁奇異章節吧!
也因此,根據廉政署調查員的描述,「白手套」和跑執照的業者每天在市府建管處走動,「跟跑菜市場一樣」。而居間扮演白手套的,還有陳菊的「市政顧問」張千鳳;他打著市政顧問招牌,堂皇進出建管官員辦公室,一手牽著廠商,一手拉著官員的手,兩邊就成交了,他自己也雨露均霑。
高雄建管處能把「賄賂」這檔事經營得像家常便飯,當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其中的關鍵有二:一是要把「行賄/收賄」的行為儀式化、常規化,大家按規矩辦事即可;二是要消除自己心裡的不安,因此相關人等均需打點照顧。所以,高雄建管處不僅有公訂價碼,每案收費一萬到十萬不等,各憑心意,這就是「價格合理」;此外,廠商和官員將這種紅包稱作「公關費」,要麻煩對方快速發照,送錢也是人情之常。既然是「公關費」,也就表示貪汙「除罪化」了?
陳菊一向標榜團隊清廉,但建管處的紅包文化顯然積弊已深,市長何以不曾聞問?何況,她自己任命的市政顧問涉足其間,這難道不是識人不明?官員因收賄「價格公道」而贏得好評,不知陳菊作何感想?
蜜月不長久 柯P應謙卑
2015-01-16 02:13:48 聯合報 拉那路/國小教師(東縣金峰)
甫上任的台北市長柯P,展現個人獨特的行事風格,有人視他為偶像,爭相合照、索取簽名,儼然成為台灣的政治明星。他的一言一行,已成為大家注目的焦點。
凡事都是一體兩面,柯P行事公斷、決策明快、公私分明、重視效率的特質,造就了有些人將他神化。但是,冷靜思考,柯P的這些優點,似乎也變成了他的缺點。
我們都知道,人再怎麼聰明,也不可能在各項領域都獨占鰲頭,尤其是在分工細密的現今社會,施政需要各種人才的集思廣益,及各局處部門的協調,才能滿足各階層的需要。
上任以來,柯P的確展現了改革的決心,他大是大非個性展露無遺。至今,許多觀察家已經看出,他強烈的主觀意識其實已經完全取代了政治協調,這樣的決策過程,其實是有其危險性的,尤其是他個人的喜好,很容易變成決策的依據,容易失去客觀性及全面性。
近日發生因為不想跳舞而當眾怒斥社會局長事件,說明柯P的決策及情緒,有加強空間。
我們樂見柯P的改革精神,翻轉不公義的現象,但也要提醒,效率考量之餘,不忘要廣納建言、展現個人風格外,不要忘了三思而後行,尤其是成為公眾人物後,更要在言語上做榜樣。
想想馬英九總統,當選之初大家視他為偶像;但是,蜜月期過後,他的聲望開始走下坡,甚至成為台灣史上民調最低的元首。我們期待柯P時時反省自己,謙卑的為民服務。
權威與威權:領袖、老闆、朕
2015-01-16 02:01:39 聯合報 社論
北市信義警分局長李德威遭柯文哲當眾訓斥後,於日前提早申請退休;柯文哲對待自己由台大醫院拔擢至市府的社會局長許立民同樣不假辭色,當眾變臉發飆,給他難堪。諸如此類的官威,包括要求同仁七點半開會、除家人以外的飯局要登錄、稱蔡璧如是他的「血滴子」等等,在在展現了他的強勢領導風格。柯文哲有四年任期,大家都在關注這樣的領導作風將如何發展。
柯文哲是政治素人,不接受官場習氣及制式框架的束縛,對習於迂緩繁縟的官僚體系,當然有正面意義的刺激。但除期待素人新政能帶來清新活潑的風格外,我們也要提醒柯市長:急診室裡的目標清晰、環境單純,威權式的上下指揮或有其必要;但民主政治的考慮多面,更需要眾人協力合作,所需要的領導藝術是截然不同的。
李德威事件之所以引人側目,不是因為柯文哲對於法輪功遭愛國同心會攻擊事件多麼重視,而是他對分局長這個「人」的當眾辱罵。市長是市警局的老闆,也是信義分局長的大老闆,他當然可以對屬下提出要求;但是,似乎不需要用羞辱的方式吧?畢竟,市政府的工作比台大急診部複雜太多,除業務龐雜、分工細膩、員工眾多,內有議會制衡、外有市民監督,周邊更有無數利益團體與公民組合環伺等,這絕非市長一人之力足以應付。因此,首都市長不應該是老闆(boss),而應該是領袖(leader)。而老闆與領袖的差別,正是柯文哲需要體會與酌量的。
老闆管理的事務通常面向單純,目標也不複雜,所以其工作重點不外乎下指令、行考核、驗成果;但做領袖則不這麼簡單,這麼制式。領袖的工作不是一種「個人秀」,而是要帶動一個團隊,使其士氣高昂、鬥志旺盛,各個層級主動發揮、積極負責,願意同心協力以助團隊開創佳績。這種「讓龐大機器協力運轉」的本事,當然與領袖的個人能力有關;但更重要的是,他對團隊要能鼓舞、授權、支持,喚起大家共同的使命感。這種領袖風範無以名狀,英文以抽象的leadership涵蓋。相對地,老闆不太需要靠風範調動下屬的積極性,英文裡bossy這個字就只剩下頤指氣使、跋扈飛揚的老闆架子。
好的領袖未必需要有一五七的高智商,但他們的EQ應該都不低,重點是能夠請到一群智商一七五的人進入團隊,共同發揮功能。好的領袖未必要求團隊配合自己的習慣(七點半開會),而是儘量在尊重個別差異、發揮各人長處的情況下,要求成員彼此配合。好的領袖賞罰分明,但不應該設一個血滴子,讓團隊走在空曠處還得擔心尊嚴受辱。別忘記,柯團隊所延攬的局處首長如果真是人才,便也應該是有自尊、有能力、成就斐然的菁英,尊重猶恐不及,豈能隨便點名管束或言語奚落?
我們不想對信義分局長的事件多做評論,但任何職位所需的條件,都是「相對於這個條件有優勢的人」才會來應聘。因此,如果像坊間傳言,某企業大老闆會要求副總經理當眾下跪,那麼會來應徵副總的,當然多是「視下跪為無物」的膝軟腰輕之輩。如果局處長如住院醫師一般每天早上七點半要開會,不在意頭上籠罩著「血滴子」的陰影,與人吃飯需要報備,自己的決策被市長一句不著邊際的話就輕易否定,那麼甘願就任局處長的,恐怕也多為缺乏專業尊嚴、責任感與自信心的諾諾之輩。這樣的官員,能夠期待他們主動負責,擇善固執,心念城市的發展遠景與廣大市民的福祉嗎?
柯文哲上任至今,做了若干堪稱大快人心的決定,包括速拆忠孝西路公車道、宣示三個月內拆除數百戶頂樓違建、議員關說上網公告、為護樹而重新檢討工程等等。即使一些決策顯得草率反覆,彷彿心血來潮便可決定政策方向,我們對於柯市長的明快作風願給予善意的肯定;但是,他對於人的缺乏尊重,當眾頤指氣使,動不動就否定他人,則露出了其威權、不可挑戰的一面,這恐怕是他最大的民主教養弱點。
好的市長應該是領袖,而非老闆,當然更不是「朕」。好的領袖吸引人才、善用人才,而非使喚奴才。厲害的老闆令「害怕的都不敢來」,但傑出的領袖卻使「有能力的都願意來」。此中高下,應該是不難判斷的。
查稅風波 柯爸:借兒子錢 需立借據嗎?
2015-01-12 17:25:09 聯合報 記者郭政芬╱即時報導

柯媽不滿說,三、四年前的事情,突然要被查稅,當然會覺得不舒服,連先生都覺得麻煩,乾脆今天拿存摺讓國稅局影印存證。記者郭政芬/攝影
分享
柯爸今天證實,上周五和今天早上都到新竹國稅局說明,他也把銀行帳簿讓國稅局查看,讓國稅局了解是何年何月匯款過去。
至於新竹國稅局詢問是否有借據或契約?柯爸回應,父親與孩子的關係,當然沒有借條。他向國稅局說明,曾有學生急需用錢,他借了學生一百萬元,也沒有要學生簽下借據,「連借學生急用錢都沒寫借據,何況是自己的孩子呢?」
柯爸指出,當初將兩老的養老金拿出來,加上二兒子也提供部分金錢,由兩老借錢給柯文哲,主要是買房子用,也說明這些錢必須要還,並沒有所謂的贈與。
柯媽補充,他們借了一千萬給柯文哲買房子,還收了兩年的利息,直到這次柯文哲台大停職,才暫時沒有向兒子拿利息。
「借給兒子的錢,還需要借據嗎?」柯媽則不滿,三、四年前的事情,突然要求查帳,當然會覺得不舒服,連先生都覺得麻煩,乾脆今天拿存摺讓國稅局影印存證。

柯爸今天證實,上周五和今天早上都到國稅局說明。記者郭政芬/攝影
父母遭查稅 柯:請國稅局夠大的出來解釋
2015-01-12 15:52:25 聯合新聞網 綜合報導

柯文哲父母 圖/擷自王定宇臉書
分享

圖/擷自王定宇臉書
分享
前民進黨台南市議員王定宇今(12日)在臉書爆料說,台北市長柯文哲的父母因為借一千萬給兒子買房子,這兩天遭國稅局查稅。柯文哲知道消息後,批評國稅局的做法已經超越社會中一般人民的忍受範圍,「請國稅局『夠大的』出來解釋」。
柯文哲在選前曾自爆,曾向父親柯承發借一千萬元買房子還沒還,今日王定宇則說,國稅局要求柯父出示借據,還要他們到新竹國稅局說明,柯父配合說明,但困擾借錢給兒子怎麼會寫借據呢。
柯文哲言談間表達對國稅局的不滿,他問道,這個國家沒有其他事要做了嗎?什麼時候國家變得那麼勤勞?希望國稅局大咖可以給他個解釋,他再決定要怎麼回應。
柯文哲父母遭查稅,網友反應兩極,有人認為,國稅局怎麼不先去查頂新或連家?也有人表示,這麼大筆的借貸金額,被查稅很正常。
【聯合報/記者邱瓊玉/即時報導】
民進黨籍前台南市議員王定宇今天在臉書爆料,指台北市長柯文哲的父母,這2天遭到國稅局追查當初借錢給柯文哲買房的借據,甚至被邀請到新竹國稅局說明。
對此,柯文哲表示,選舉已結束,選舉期間,國稅局去查過去幾年的稅,已很惹人反感,父親昨天還到國稅局解釋,這種做法超越社會一般人忍受的範圍。
柯強調,政府機關當然可以查,請國稅局出來解釋想法是怎樣,「我才來決定我的回應是什麼」,他並四度強調,要請國稅局「夠大的人」出來解釋,按照對方的解釋,再來決定自己的回應。
柯文哲說,國家沒有其他的事情要做是不是?難道我們的國家變得這麼勤勞嗎?希望國稅局公開說明。
柯P父母遭查稅 國稅局:無針對性
2015-01-12 16:40:10 聯合報 記者沈婉玉╱即時報導
針對台北市長柯文哲父母被查稅一事,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說明,因民眾檢舉柯市長向父母借款買屋,依財政部訂定的「各級稽徵機關處理違章漏稅及檢舉案件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各級稽徵機關於稽查或審理違章漏稅及檢舉案件時,為調查事實及證據的必要,得以書面通知受稽查人,攜帶有關帳據限期到達辦公處所,以供查核並備詢。
國稅局澄清,對於民眾檢舉案件,均一律依上述作業要點辦理,並無針對性查稅事宜。
【中央社/台北12日電】
有人檢舉台北市長柯文哲向父母借貸買房一事,財政部北區國稅局表示,接獲這類檢舉時,會依規定發出書面通知受稽查人來說明,並未針對性的查稅。
財政部北區國稅局指出,北區國稅局函查柯文哲向父母借款買屋一事,主要是全案為民眾檢舉案件,依財政部訂定的「各級稽徵機關處理違章漏稅及檢舉案件作業要點」第6點規定辦理。
北區國稅局指出,各級稽徵機關於稽查或審理違章漏稅及檢舉案件時,為調查事實及證據必要,得以書面通知受稽查人,攜帶有關帳據限期到達辦公處所,以供查核並備詢,北區國稅局依相關要點規定辦理,並未針對性查稅事宜。
本文於 修改第 5 次



 本城市首頁
本城市首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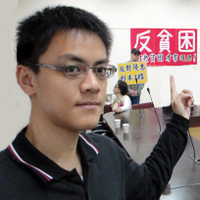









 】
】






